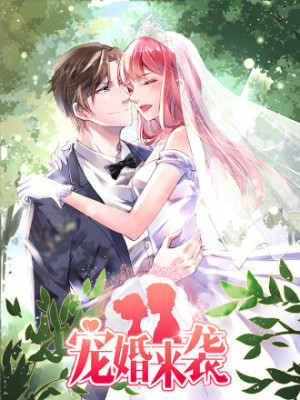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
在所有关于双子塔的摄影作品中,最触动我的不是爆炸和废墟,而是1997年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英文版的封面用图。画面的背景是云遮雾绕的世贸中心双子塔,前景则是一座教堂的山墙和十字架的剪影,右上角还有一只形状如同飞机的海鸟。这些视觉元素以一种诡异的未卜先知,暗示了这个城市来自空中的危险以及即将升腾的爆炸烟雾。事实上,在世贸中心遗址对面不远处,就有一座建于1766年的圣保罗礼拜堂,那里还竖立着曼哈顿岛上一些先民们的古老墓碑,它们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久远。这个教堂在1970年代见证了世贸中心大楼充满争议的修建过程,也在21世纪的头一年见证了作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象征的双子塔的爆燃和垮塌。尽管双子塔倒塌时能量极大,周围很多建筑受到冲击,但近在咫尺的圣保罗礼拜堂却安然无恙,这的确是9·11事件中一件不大不小的神迹。于是,在纽约消防员和警察抢险救灾的最初几周里,这个教堂成为了“归零地”(Ground Zero)旁的一座“圣殿”,不仅是市民们悼念亡者的地方,也是换班消防员临时休息的场所。
2008年夏天,我作为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访问学生,第一次来到美国。初秋的一次纽约之行,我特意去看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废墟,刚好路过这个古老的教堂,就进去参观。让我惊讶的是,里面还保留着当年救灾人员用过的行军床,还有用牺牲消防员的照片和纪念徽章装饰的纪念角。在布道讲坛的上方,悬挂着一个醒目的条幅,写着“俄克拉荷马人民与纽约同在”。当时我突然想到,在9·11之前,美国本土发生的最大一次恐怖袭击,正是在俄克拉荷马——1995年,那个叫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的人将7000磅的炸药装在卡车上,运到俄克拉荷马城联邦政府大楼楼下引爆,造成了16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不过,与9·11的19名劫机犯不同,麦克维是美国白人,而且作为海湾战争的老兵,他甚至还自诩为“爱国者”。麦克维被执行死刑的时间是2001年6月11日,当时美国人或许舒了一口气——毕竟,这个在美国本土制造了最严重的恐怖袭击的人被处死了。但谁能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更大的悲剧发生了!
也是在2008年,我作为博士生访问学者在马里兰大学英文系旁听了琳达·考夫曼(Linda Kauffman)教授的“美国当代小说”课。她在课堂上特别推崇的书,正是德里罗前一年刚出版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那本书的封面,同样令我印象深刻:业已消失的双子塔耸立在万米高空的云海中,作为世俗之物的摩天楼仿佛被赋予了一种“后现代崇高”。考夫曼教授在课堂上拿着这本书告诉学生们,美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终于用小说对那次改变世界的恐怖袭击做出了回应,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美国批评家们已经等待了很久。正是在那个时刻,我萌生了研究9·11文学的想法。
时光荏苒,14年过去了,我的生活和这个世界一样,已经有了太多变化。2019年8月,我再次作为富布赖特项目访问学者,带着家人来到弗吉尼亚的夏洛特维尔生活学习。此时,人们似乎不再经常提起9·11,但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大事件,又和那次恐怖袭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它们成为该国史上最旷日持久的战争,时间超过了越战、“二战”和美国内战;原本被认为针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恐怖袭击变身为全球恐怖主义,如病毒般侵袭伦敦、巴黎、马尼拉、孟买、内罗毕、摩加迪沙、布鲁塞尔、奥斯陆、基督城等等,极端分子对平民制造的杀戮每隔一段时间就成为世界新闻的头条;“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触发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危机,造成了欧洲史无前例的难民潮,由此又间接引发了英国脱欧和极右政治势力在欧洲多国的兴起;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在“后9·11”时代登上了美国政治舞台,他推行强硬的反移民立场和政治单边主义,引燃反全球化的贸易战……
在这14年里,不仅世界有了不一样的面貌,美国文学、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也都有了重大变化。有更多涉及9·11、恐怖主义、反恐、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小说相继问世,当中不乏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有些已经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项。诚然,严肃文学对于9·11及其之后世界变化的再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文学绝不只是时代风潮的传声筒,而是积极参加了话语生产和媒介化过程,并以文学独特的内省、多元、共情和含混,介入“后9·11”文化的众声喧哗中,对抗大众媒体和国家机器的垄断性话语。美国批评家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说过:“文学是最充分、最全面地思考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的人类活动。”[1]鉴于9·11事件及“后9·11”状况的复杂性,文学家当然会直面这一挑战,并将之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母题加以书写。
在谈论9·11文学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先对我们耳熟能详的9·11事件做一番历史梳理。但其实更重要的前期工作,反倒是先理解何为“事件”(event)。在《韦伯斯特字典》(Websters Universal Dictionary)中,event的释义是“某件发生之事(尤其指重要或瞩目的事)”。如果考察一下词源,我们会发现它来自拉丁语evenire,意思是“出现、到达、发生”,往往意味着“变化、影响”。[2]这样的字典解释看似无甚稀奇之处,但对于当代西方哲学家而言,event却是一个殊为复杂的关键概念。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事件是与历史的断裂联系在一起的,事件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社会规范和知识系统的观念重构。对巴迪欧(Alain Badiou)来说,事件有着更为核心的本体论地位。在《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中,巴迪欧说“事件”不是事物秩序产生的“影响”,而事物秩序的“断裂”(rupture),正是在这种断裂中真理才得以开启。[3]德里达亦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事件意味着“一种绝对的惊奇”[4],并认为它“具有无限的秘密形式”[5],无法被理解和预设。
由此可见,对于哲学家而言,事件并非简单的“发生之事”,而是对我们日常生活、常识规范乃至历史进程的一种打破。在巴迪欧的视野里,最典型的“事件”是耶稣受难、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纳粹屠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恐怖袭击才成为一次事件。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规模之大(19人同时劫持了四架波音客机)、伤亡之巨(2977人因此殒命,还有更多的生者因为各种后遗症,遭遇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和影响之广(亿万观众在电视和互联网直播中目睹北塔被另一架客机撞上,目睹双子塔先后倒塌),更是因为它的意义栖居于暧昧不明的历史地带,因为我们对这个“到来之物”的理解仍然处于永恒的延宕之中。
那么,当我们在谈论9·11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棘手(如果不是无解)的问题。9·11的事件性决定了它不能仅仅在既有的历史认识框架里被理解和阐释,与此同时它又比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历史事件更具有当代性。所以,9·11带来的后续影响非但没有终结,反而正在我们当下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文学想象和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发酵、显露、变形。我们对它的认识不仅无法一蹴而就,而且可能就在我们谈论它的下一秒,某个极端分子自杀式炸弹会在巴黎、纽约、孟买、悉尼或伦敦引爆,使得我们对9·11的理解瞬间就会变得不同。试问,在当年曼哈顿目击那次恐怖袭击的时刻,谁会想到全球恐怖主义的病毒会在今天蔓延得如此猖獗?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无法彻底跳脱9·11来看今日之世界——反恐战争、“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伦敦恐怖袭击、“虐囚门”、伊拉克战争、“棱镜”计划、斯诺登、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的兴起、巴黎恐怖袭击、欧洲难民危机等等,无不直接或间接源于星期二的那次事件。
这次恐怖袭击深刻定义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与困局,它早已超出了某个一时一地的突发事件的孤立影响,成为全世界被恐怖主义袭扰的象征性开端。斗转星移,十几年后,当恐怖主义的阴影已经无比真实地潜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终于发现,其实没有哪个国家和社会可以在全球恐怖主义的肆虐中作壁上观。行文至此,我想到了一个叫吕令子的女孩。9·11发生的那一年,这位沈阳女孩年仅12岁,即将升入东北育才学校(东三省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之一)就读,而沙尼耶夫兄弟俩在那一年刚追随父母,从动荡的车臣辗转来到美国生活。后来,这位中国女孩飞跃重洋赴美留学,就读于波士顿大学。2013年4月15日,就在她与同学围观马拉松比赛时,沙尼耶夫兄弟俩放在垃圾箱里的自制炸弹突然爆炸,夺去了她年仅23岁的生命。
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是9·11后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一共造成三人死亡,吕令子是其中的一位。生于1993年的恐怖分子乔卡·沙尼耶夫被捕前藏在一个民宅院子中的小艇里,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作案的原因:报复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对穆斯林的打击。他还在游艇的船身上留下了两个英文单词:“Fuck America”。吕令子之死就像一个寓言,深刻描述了在“后9·11”世界,原本远隔万里、毫无瓜葛的人们如何被诡异地联结在一起,并在突如其来的杀戮和报复中,共同沦为恐怖活动的牺牲品。所以,我始终认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无论国籍、肤色、信仰或阶级为何,对恐怖主义都没有置身事外的幸运或冷眼旁观的特权,这是由我们所处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学者,我感到这样的时代的文学艺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不仅是因为恐怖分子使用的极限暴力最大限度地劫持了大众传媒的关注和想象,从而与文学艺术构成了竞争关系,更是因为恐怖主义暴力背后隐藏的逻辑,与文学艺术所试图追求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如德里罗在一部小说里所言,“(小说家追求的是)含混、矛盾、低语和暗示。而这恰恰是你们(恐怖分子)想去摧毁的”[6]。恐怖暴力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制造了一种恐惧的政治,而大众传媒往往受到资本的挟裹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无法真正深入地清理这种暴力对于社会肌理的巨大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我深感全世界的文学批评家亟须在当下展开行动,去对21世纪陆续产生的9·11文学作品做出有价值的阐释和批评,并以此为契机去推动更复杂深远的意义生产。我坚信,9·11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曼哈顿“归零地”一时一地的灾难事件,而应在现代性造成的历史断裂线中,寻找和反思这种暴力的缘起与流变。
* * *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将9·11和与之有关的文学作品/文学事件放在宽泛的历史语境下加以解读,希望获得更大的历史景深。一方面,发生于新世纪伊始的9·11恐怖袭击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譬如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景观并被不断地媒介化),它不是任何战后地缘冲突的简单复现,而是构成了当代全球史的断裂点。另一方面,围绕9·11的国家悲悼和媒体再现往往受制于一种简单化的文化逻辑,具有不言而喻的短视性。西方主流文化对9·11的悲情化再现,让“归零地”仿佛具有了某种神圣的意义,让纽约的受难者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排外的道德共同体。9·11主流叙事往往显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恋,以及全球帝国意识形态的褊狭,因此批评家需要关注那些具有真正历史思维的9·11文学作品,将这次恐怖袭击放到奥斯维辛、广岛、德累斯顿、俄克拉荷马等历史坐标构成的连续体中加以讨论。
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实践的批评方法,正是这样一种基于历史联结的文本话语和审美分析,既重视产生现代恐怖主义的具体而微的时代语境,也观照恐怖对各个时代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心理意识的深远影响。恐怖,不只是当代反全球化极端力量的暴力宣泄和话语宣传,也自古以来就浸淫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及内部冲突中。只有当我们以更复杂、更历史的思维来看待这种特殊的暴力形式,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他者之怒。当然,对9·11小说中的恐怖话语进行分析并不容易,因为这种话语的语用效果往往是含混的,而且恐怖事件往往不能凭借行动说出自身。换言之,恐怖分子想说的,和他们的恐怖袭击实际上说出的,以及受众接收到的,常常会有着天壤之别。行动一旦转为语言,会带来巨大的个体理解偏差,也将在不同的阐释共同体中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转译和中介化。按克莱默(Jeffory A.Clymer)的说法,恐怖分子依赖的语言模型之所以往往无法奏效,是因为行动的受话方是异质的听众,“他们的态度、同情心和政治立场会有巨大的差异”[7]。
这种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巨大罅隙,使得一些研究者主张对恐怖主义的研究需要采取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立场,甚至强调恐怖主义事件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本化的建构,它没有任何脱离语言本身的实质意义。当代人类学家艾伦·费尔德曼(Allen Feldman)就认为:“(事件的)顺序和因果性既是一种道德建构,也是隐喻建构,所以事件并非实际发生的。事件是可以被叙述的东西。事件是由文化所决定的意义组织起来的行动。”[8]费尔德曼通过对北爱尔兰暴力史的民族志写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即“叙事集团”(narrative bloc),强调暴力叙事生成过程中的多重变量。在这个模型下,事件(event)、作用方(agency)和叙述(narration)三者构成了“叙事集团”,这种集团是“一种弹性的组织,涉及语言、物质化的人工制品和关系。关于暴力的叙事集团调动了星丛般的事件和关于事件的话语,从而构成一个大写的事件”[9]。与费尔德曼类似,祖莱卡(Joseba Zulaika)和道格拉斯(William A.Douglass)在影响深远的《恐怖与禁忌》(Terror and Taboo)一书中,甚至宣称“不管它还可能是别的什么,恐怖主义是印刷出来的文本……恐怖主义是制造情节行动的文本,叙事顺序是一种道德和话语的建构”[10]。
诚然,9·11文学批评关注的不只是一个大写的事件,而是围绕9·11产生的“叙事集团”,它体现了恐怖事件和社会、媒介、语言、叙事的复杂牵扯与勾连。然而,我们也需要警惕单纯从后结构主义立场(无论这种思想资源和批评实践是来自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还是别的学科)出发的恐怖主义研究。对于那些亲历恐怖创伤的人来说,恐怖主义也只是“印刷出来的文本”,而缺乏任何本质的真相吗?将事件性归结为叙事的建构,这实际上已经在向相对主义的后现代诡辩术立场发生危险的移动。因此,本书既看重9·11事件在叙事上的多义性和媒介化过程中的建构性,同时也会认真思考9·11事件给生命个体在情感维度上带来的影响,这涉及创伤、悲悼、共情、记忆等多个方面。
第一章“艺术与恐怖”将首先尝试以一种“去9·11化”的方式来思考9·11事件。或者说,在准备谈论9·11之前,我们需要先朝历史的源头眺望,思考艺术与恐怖之间的暧昧关系。从艾柯论丑的历史,再到伊格尔顿对《酒神的女祭司》中“神圣暴力”的考察,一个不便言明的历史真相浮现出来,即:恐怖和文明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的,虽然后者常自诩理性的价值观,并妖魔化自身文明之外的他者,但在人类文明得以确立秩序的过程中,无处不见恐怖的阴森鬼影。浪漫主义以降的现代艺术(尤其是先锋艺术)曾热切地期待,希望用想象的暴力进行越界,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同一化逻辑,挽救被现代性湮没的有机个体和家园。然而,“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冲撞在我们的时代从未平息,非理性作为一种文化迷因(meme)从未在启蒙时代之后真正离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无名怨愤”(ressentiment)不断激发艺术家和恐怖分子将暴力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艺术家和恐怖分子的共谋/竞争关系,以及文学艺术在恐怖时代的特殊认知价值,构成了本书审视9·11文学的重要出发点。
第二章“见证与共同体”则是另一种对9·11文学的历史语境化。这里,我之所以强调从奥斯维辛到曼哈顿“归零地”的连续性,并非暗示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无懈可击的类比关系,而是试图从大屠杀文学批评中汲取理论资源,用于9·11文学批评。虽然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一再强调奥斯维辛之后文学再现的绝境,以及“屠犹”对于西方文化合法性的瓦解,但正如米勒(J.Hillis Miller)所言,“毒气室”悖论所造成的不可再现性,不应该成为阻挡见证的借口。相反,对这些人为灾难进行“见证”,不是在用审美符号复刻那些人类肉身被纳粹化作青烟的极端情境,而是利用文学的施为性,在法律无法触及的灰色地带,言说在奥斯维辛“人之为人”的耻辱和困局。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这是不是个人》是讲述奥斯维辛的最佳范例之一。9·11事件虽然在暴力的极端性上无法和“屠犹”相提并论,但燃烧的双子塔、绝望的受困者和坠落者同样让小说家面临着不可再现性的难题,也同样深刻触及了文学如何见证和如何反思共同体等重大问题。米勒甚至告诉我们,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的监狱里,那些穿着橘色囚服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同样处于一种阿甘本所言的“牲人”状态,纳粹集中营的幢幢鬼影在反恐战争中同样显现了出来。
第三章探讨“前9·11”小说,重点研究了梅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尔比》和康拉德的《间谍》。本书似乎仍然是在“朝后”看,然而这种策略与前两章一样,是基于对狭义“9·11小说”概念的一种解域化。我认为,9·11的前史对于理解这个当代事件至关重要。梅尔维尔笔下那个孤僻的抄写员坚持说“我宁愿不”,这种消极抵抗暗示了早在基地组织之前,就有人对曼哈顿发动了恐怖袭击。德勒兹等人认为,巴特尔比是从语言内部生发出一种恐怖的反抗力量,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它蕴含着本雅明式“神圣暴力”的潜能。甚至可以说,没有哪篇当代文学作品像这篇19世纪中期的中篇小说那样,展现了资本主义内部深刻的文化矛盾,以及极端他者的颠覆可能。同样,康拉德的《间谍》从另一个方面触及了资本主义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被媒体誉为“第一部9·11小说”的《间谍》中,康拉德以极为矛盾的态度,反讽式地剖解了19世纪末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试图对公众的想象力进行一场破袭,以及反恐的警察力量运作的隐秘逻辑。我认为康拉德无意于刻画一组无政府主义者的滑稽群像,小说家对无政府主义者及其“行动宣传”暴力的书写,不仅仅指向这场运动背后隐秘运作的人性之恶,而且代表了这位波兰外来者对英国及欧洲大陆当时反恐政治的矛盾态度。只有重返《间谍》这个反讽文本的历史构建现场,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那个时期的康拉德与新兴的全球帝国之间的暧昧关系,并由此提炼和重申这部写于20世纪初期的政治小说对于“后9·11”时代的现实意义。
从第四章“9·11小说与创伤叙事”开始,本书开始讨论传统意义上的9·11文学作品,所选文本也是当代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坠落的人》《特别响,非常近》和《转吧,这伟大的世界》。本书希望通过这一章,重新激活国内学界对于创伤叙事的讨论,这意味着对9·11小说的讨论不仅要揭示恐怖袭击如何造成了心理障碍和记忆缺陷,更要关注“创伤”作为一种批评话语,是如何在20世纪被建构和获得广泛流通的。卡鲁斯(Cathy Caruth)的创伤理论承袭了弗洛伊德、拉康、德曼等人,但其独创性在于对创伤声音的发掘,从而将创伤症候视为一种朝向他者和他者发出的“双重讲述”。然而,卡鲁斯对于不可再现性、不可理解性的过度强调,让创伤叙事最终成为反对阐释的堡垒。如果不加甄别地在9·11文学批评中沿用卡鲁斯的创伤理论,或许将进一步阻塞“我们”与他者对话的通道,让创伤凝固为一种自恋式的创伤文化。这里,我做的工作与卡普兰(E.Ann Kaplan)和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颇为相似,就是通过细读德里罗、弗尔和麦凯恩的9·11小说,从多元的、跨学科的创伤理论入手,在西方左翼和右翼主导的创伤政治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从而为“修通”(working through)历史创伤寻找建设性的方案。
在第五章“极端他者和暴力”中,我将关注点从受害者转向施害方,探究极端他者的恐怖暴力如何影响了当下社会对于普通他者的认知。本章讨论的文本是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和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两部小说的共性在于所采用的他者视角,虽然前者关注的是普通他者,后者则是极端他者。哈米德和厄普代克都在努力用9·11小说提供一种“反叙事”,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对于穆斯林他者的刻板化再现,把他者问题放入当前复杂的多元文化中加以考量。两位小说家笔下的穆斯林他者根植于9·11之后的创伤文化,昌盖兹和艾哈迈德深深浸淫美国文化,他们并不像阿富汗基地组织的那些极端分子,或慕尼黑清真寺那些密谋袭美的“圣战”者;相反,他们处于一种后殖民文化的第三空间,9·11之后美国矫枉过正的反恐让他们开始质疑并仇恨美国文化。在这种他者视角的叙事中,我们得以窥见恐怖叙事中复杂的地缘矛盾和历史记忆,也进一步认清了在“后9·11”文化中全球化面临的深刻危机。通过对阿萨德(Talal Asad)、本雅明、阿伦特、泰勒(Charles Taylor)和加缪等人思想作品的解读,我试图让9·11文学中的他者问题不仅仅停留在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异质想象中,而是为暴力批判本身找到一种更具文化包容性、跨学科性的基础。
第六章“他者伦理和共情”将焦点微调,从他者政治的领域转移到他者伦理,并加入情感研究的维度,进一步丰富9·11文学研究的理论内涵。在本章中,我同样以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为双轴,不仅涉及萨特的存在主义中的他者问题,还把列维纳斯、德里达、米勒、哈贝马斯等人放入讨论场域,从而将“后9·11”的他者伦理变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这些关于他者的伦理学思考并不是为我们处理9·11文学中的他者问题提供了现成的伦理解决方案,而是烛照了这个问题极端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如果说他者伦理试图回答的是“我们”如何与“他们”相处,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共情似乎是修复恐怖主义造成的族群和文化撕裂的最佳解药。不过,我认为共情在这里依然是问题本身,而非答案。通过对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和瓦尔德曼的《屈服》等作品的分析,本书试图传递一个看似悲观、却更为审慎的观点:跳出主体的藩篱去与他者实现共感或共情,固然是一种更为开明进步的做法,但这样的情动是基于身体的物性,往往绕过了更为复杂的情感、记忆、认知等大脑过程,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大众媒体的媒介化过程的影响。“后9·11”时代共情的限度在于它的选择性和脆弱性,作家本人亦只能借助主观想象去言说和再现共情。本章所分析的两部小说以颇为不同的立场,展现了文学艺术与叙事共情之间不确定的价值实践。
本书最后一章是“‘后9·11’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我将目光投向了伴随美国反恐战争而产生的战争小说,选择了三部风格迥异的作品来做文本细读:鲍尔斯的《黄鸟》、方登的《漫长的中场休息》和克莱的《重新派遣》。充满痛苦和诗意的《黄鸟》更像是对于美国战争文学传统的一种继承,士兵在异国战场经历了道德的成长,并需要面对战争带来的无解的存在主义危机。《漫长的中场休息》则通过高密度的讽刺,透过一个从战场暂时归来的英雄连队的视角,展现了美国战争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从而体现了伊拉克战争的当代性。短篇小说集《重新派遣》是首部荣获“国家图书奖”的伊拉克战争题材作品,克莱的新意在于多视角、多主体地反思伊拉克战争复杂且矛盾的多重面相,而非单纯地书写反战主题和“战壕抒情”,或重复从前战争文学经典中的“战场诺斯替主义”。我认为,反恐战争的后人类技术形态和媒介化特征,赋予了这些新型战争小说某种独特性,它们对战争话语在美国“后9·11”社会构建的新现实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介入,从而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战争中正义、创伤叙述和士兵责任等问题。
时至今日,9·11作为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依然在不断地带来余震和涟漪,它没有向我们昭示它的终极意义。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我们已经并且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生活在“后9·11”的历史情境下。必须承认,虽然本书酝酿了多年,但对于9·11及其文学再现这样处于不断生成中的当代事件,我依然不可避免地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中。书中的某些观点或许很快就会被瞬息万变的世界地缘政治、新型互联网文化、后理论人文思潮和大脑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所否定或更新。21世纪的未来会往何处去?严肃文学是否会在互联网化的大众传媒和恐怖分子的夹击下日益萎靡?文学艺术是否还能对极端暴力做出有力的言说,并改变人类的观念?这些问题都是本书希望回答但又无法给出满意答案的。它们既是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挑战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它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去参与批评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去继续捍卫这个狂暴时代文学艺术的合法性和深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