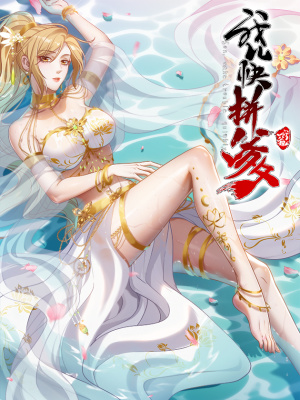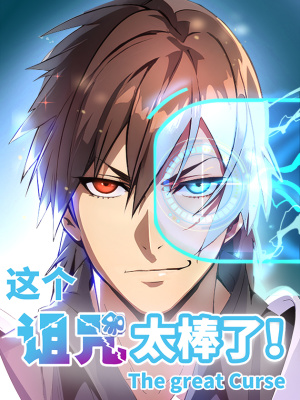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
寒风呼啸,裹挟着漫天飞雪在天地间肆虐。一座低矮的茅屋在狂风中摇摇欲坠,茅帘被吹得猎猎作响,仿佛下一刻就要被狂风撕碎。
茅屋内,一盏残灯如豆,昏黄的光晕洒在三人身上。
“咳咳咳——“
老楚一阵剧烈的咳嗽,'哇'地呕出一口黑血。他枯瘦的手死死攥紧被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床榻前,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别过脸,不敢看木盆里那滩刺目的黑血。四娘忙拿出一方粗布手帕,为老人拭去嘴角的血丝。
“天一亮,儿媳就进城把张大夫请来...”四娘声音发颤道。
老楚无力地摇头,喉间发出“嗬嗬“的喘息:“不必了...我的身子...自己清楚...“他突然瞪大浑浊的眼睛,“只是...我走后...小毅就交给你了...”
“阿翁...”四娘眼眶通红,咬着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儿媳...会将毅儿抚养长大,将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一样也不落下。”
“儿媳知道,阿翁想让毅儿上学读书。阿翁放心,我会让毅儿有学上,有书读,以后让他做个读书人...出人头地!”
老楚早已病入膏肓,连张大夫看了都摇头叹息,说老楚能撑到现在,全凭一口气吊着。
听着四娘一字一句说完,老楚紧绷的身躯似乎放松不少。可随即,他的目光落在四娘身上——粗布衣裙,身形瘦弱,原本清丽的面容如今也因操劳而显得憔悴许多。
“当初……若不是吾坚持让大郎去从军,吾儿就不会战死,你也不会失去丈夫,如今成了守寡,小毅才六岁……就不会没了爹爹。”
老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到以后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一时悔恨无穷。
四娘无奈摇头,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当年若不是父亲为了为了抬高她的身价,四处宣扬说什么“眉间一点痣,天生旺夫命...”。老人听了,这才登门,用家里唯一的老黄牛做聘礼,嫁入楚家。
可如今呢?
旺夫之命?同去从军的人里,唯独只有大郎没能活着回来。
四娘垂首,两行清泪忍不住从脸颊上流下。她瘦削的肩膀不住轻颤——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命如纸薄。
“四娘......“老人喉头滚动,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你如今...也不过二十出头......往后...找户好人家嫁了...“
“阿翁何出此言!”
四娘倏地抬头,眼中泪光闪烁,却带着几分倔强。
“儿媳虽只是一介蠢妇,但也知道‘从一而终’的道理。”
她“扑通“一声跪到在地,一把扯下头上木簪,那簪子“咔“地一声折成两截,被她狠狠掷在地上。
四娘举起三指对天:“儿媳今日对天起誓:生是楚家人,死是楚家鬼。此生绝不二嫁...”
“不可...”老人急得咳嗽起来,枯瘦的身子猛地前倾。四娘慌忙托住他的后背,隔着粗布衣衫都能感受到嶙峋脊骨。
“傻孩子...”老人喘息着摇头:“你可不要多想...女子改嫁,本是天经地义...当年我娶你婆婆时,不也如此...这世上人活着已是不易。”
“我知你贤惠孝顺...”老人浑浊的眼中泛起泪光,“这些年...苦了你...“
“阿翁,您别说了!“
四娘不忍地打断,用袖子抹去眼泪,强稳着声音道:“开春了,我就送毅儿去书院发蒙。阿翁无忧,儿媳可以养蚕织布,入冬了便进城做些缝补浆洗的活计,无论如何...“
老楚望着四娘坚毅的神色,不禁深吸一口气:“若毅儿有此读书天赋,便让他做个读书人……若是不听教化,不求上进,便让他做个寻常百姓。“
四娘重重点头。老楚又转向小毅:“毅儿...以后爷爷不在了,你要听你娘的话。不要学爷爷...心比天高...到头来...“话未说完,便剧烈咳嗽起来。
“爷爷,我会听娘的话。“小毅怯生生地应着,小手攥紧了母亲的衣角。
老楚说完这些,终于不再言语。他喉头动了动,似乎还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深深叹了口气,枯瘦的身子重新躺下。
窗外,风雪更大了。
恍惚间,老人的思绪飘回了数十年前——
那一年,十五岁,少年兴冲冲地跑回家,对父亲喊道:“爹!儿子要去当兵!”
二老闻言,满是惊异。这年头,谁不是躲着兵役?宁愿躲到深山当野人...还有人上赶着要去当兵的——这怕不是傻子?
原来,这一年,赵国有一名将,十八从军,二十一岁便做了大将军,拜将封侯,名动列国。少年听了,于是也要学人当兵从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
“儿啊!“母亲苦口婆心劝道,“当兵打战除了会死人,哪有什么建功立业可言?书上说的也不可全信,若是打了胜仗,也是将军们得了封赏,你一个小兵,还能落着什么好?若是侥幸活了下来,那时也是缺胳膊少腿,便是连媳妇儿都讨不着,才让人笑话呢。”
只是,不管为娘的如何劝说,少年都不为所动,更是私下里瞒着家人报了名,等二老知晓时,军帖都已送到家里来了。
渭城,望乡台。
离开的那一天,二老哭得很是伤心。母亲拉着少年的手泣不成声:“三儿啊,娘知你孝顺。可...你大哥二哥躲还来不及,你怎就偏要去...“
同行当兵的人里面,只有少年意气风发,仿佛前方等着他的不是生死难料的战场,而是封侯拜将的青云路。
少年跪下,给二老磕头,并学着书里说道:“儿子不孝,以后不能给二老尽孝了。然则儿此去,上则报效国家,全了忠孝之名;下则沙场建功,出人头地,此大丈夫所为,亦儿所愿也。虽马革裹尸,纵死无悔,母亲勿念。”少年一去不返。
十五从军征,一去十五年。
归来时,已是物是人非。少年已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少年,断臂残躯,得了些许赏赐,独自而还。再到家时,只见茅屋残破,空无一人,才知道父母兄弟俱已不在。原来有一年大旱,不知是饿死了,还是病死了。
村里老人告诉他,自己走后,母亲时常念叨一首民谣:
望乡台,望乡台,年年此处送征人。
东家死了西家亡,年年征战人未还。
......
少年给自己取名一个“离”字,楚离。常人只以为“离”是离别、离散之意,只有老楚自己心里清楚,当兵时,曾听人说古时有个叫要离的人,他杀妻儿、断臂残身,只为换得一朝出人头地、光大门楣。老楚觉得终有一日,自己也能出人头地,光大门楣。
老楚三十多岁,娶了邻村的寡妇为妻,生下一子叫大郎。不久,寡妇病死,老楚一个人把大郎拉扯大,对大郎寄予厚望,希望子承父业,从小就教育大郎将来要出人头地,建功立业。
大郎十八岁,老楚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姑娘姓陈,叫四娘,家住陈家村。听人说四娘不仅生得容貌出众,而且有贵人之相,娶之,宜室宜家,还能旺夫。老楚本不信命,但这一次,却是花了大价钱,亲自上门求娶,促成了这门亲事。
四娘嫁给大郎后,不久便有了身孕,然而,还没等到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老楚便让大郎去从军。大郎本不愿从军,周围的人也纷纷劝老楚,说:“大郎是独子,交些钱财免了兵役...”
老楚却说:“大丈夫自当建功立业,岂能一辈子无所作为……”
......
自从大郎死后,老楚便成了全村笑话,都说他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到头来,误人误己一场空。”
有人曾问他:“出人头地...真有那么重要?”
老楚不甘心,为什么有人生来富贵,一辈子锦衣玉食,衣食无忧;有人却是衣不蔽体,饥不果腹,终日劳作却是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时也,命也,是天命已定?还是自己无能为力?
老楚不知道,该如何做?
只记得幼时,家里时常没有饭吃,自己与大哥、二哥争抢...母亲总是把自己的那份给他。夜里听见母亲辗转反侧,二哥说:“娘是饿得睡不着...“
“原来...”
昏暗的屋子里,老人喃喃自语:
“这一生...”
“至始至终...什么也改变不了...”
这一刻,老楚缓缓闭上了双眼,一滴浊泪顺着眼角滚落。忽然,又睁开了双眼,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
“四娘!“
“要是毅儿将来有出息...“
“记得告诉我一声...“
“一声就好...“
说完,那只独臂终于无力地垂下。可那“出人头地“的执念,至死也没能放下。
“阿翁...”
“爷爷...”
......
累土为坟,草席裹身,四娘听从老人生前遗愿,没有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