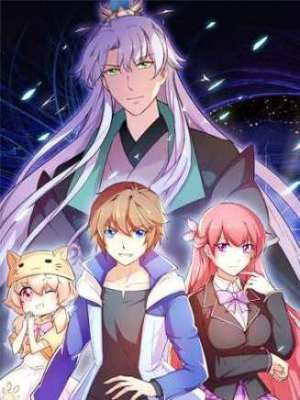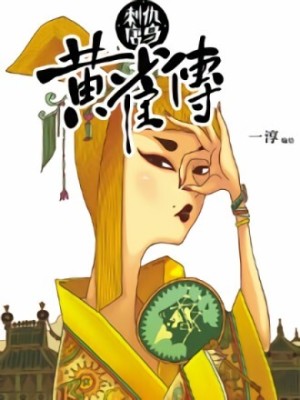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
公元2065年,一个与我们所知截然不同的平行宇宙。
天上,“霓虹穹顶”——奇点集团悬浮于城市上空的庞大反重力复合体,是索伦的空中堡垒,也是其“沉默计划”的总控制中心。白日里,它特殊的外壳材质折射着太阳冰冷的光芒,如同苍穹之上的一块巨大、无瑕、充满了非欧几何般诡异切割线条的晶体结构;夜晚则散发出令人迷醉却又带着一丝不祥预兆的、如同深海巨兽呼吸般明灭不定的霓虹辉光,像一枚别在无尽黑色天鹅绒上的、散发着冰冷科技神性的巨大徽章,以一种近乎永恒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着下方喧嚣、拥挤、被无形数据流彻底渗透、格式化的星球。它时刻提醒着地面上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被焦虑和绝望反复噬咬的、渴望着某种终极解脱的人们:那里是“秩序”与“纯粹”的应许之地,是摆脱这具沉重、易朽、充满了非理性冲动和低效情感的肉体凡胎的数字乐土,是索伦承诺的、远离“地气”污染的、绝对“寂静”的最终归宿。
地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类头颅里,都跳动着同一枚芯片的心脏——BRC,生物谐振密文芯片。它像一条无形的、植入神经的脐带,将每一个孤立的个体意识强行接入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奇点网络,将思想的细微波动、情绪的起伏涨落、甚至梦境残留的破碎光影都精确地量化、分析、并转化为冰冷的、可流通的神经货币(NC),成为驱动这个庞大社会机器高效运转的血液。BRC不仅仅是连接器,更是调节器、优化器。它调节情绪,抚平那些被定义为“负面”或“低效”的极端情感波峰,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稳定”与生产“效率”。记忆可以付费下载更新,虚拟的感官体验可以按需购买填充空虚,痛苦和悲伤?只需轻轻一点,就可以暂时屏蔽,如同关闭一个恼人的后台程序。最终极的商品,也是最终极的消费,是意识上传,将自我转化为纯粹的数据流,获得那虚无缥缈却又被宣传得令人趋之若鹜的“数字永生”。
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决心,试图将粗糙、混乱、充满肮脏意外和低等欲望的现实彻底格式化,绘制一幅绝对理性、完美无瑕、所有变量皆在超级AI——BRC-Core掌控之中的数字画布。
然而,画布之下,那古老的、属于这颗星球本身的底色并未完全褪去。在摩天楼群冰冷的阴影与流光溢彩、不断变换内容的全息广告牌的缝隙间,在被网络遗忘、信号衰减、地图上仅标注为危险“未定义区域”的“例外区”,在乌蒙山连绵起伏、如同大地古老伤痕的褶皱深处,在赤水河浑浊、奔腾不息、仿佛承载着被文明遗弃的远古记忆的流水中,一种被称为“地气”的、属于前数字时代的、近乎神秘却又真实存在的本源能量场,如同沉睡了亿万年的、星球本身的意识集合体,仍在以其自身宏大而缓慢、非线性的节奏,无声地呼吸、脉动。
它混沌,复杂,充满原始的、野性的生机,也潜藏着未知的、足以颠覆整个数字秩序的、可怕的危险。
它是这幅看似完美的、冰冷的数字画布上,那永远无法被彻底擦除的、属于地球本身的、活生生的、带着温度和脉搏的——底色。
--------
生物谐振密文芯片(BRC)的唤醒程序,总在清晨六点零三分准时启动,不多不少,精确到毫秒。那段被精心调制过的α波音乐,平缓得如同心电图停止前的最后几秒,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如同远古祭祀般的低沉嗡鸣,意在将个体意识从睡眠的混沌中“优化”至清醒的工作状态。沈星常常在想,那多出来的三分钟,究竟是奇点集团的工程师们经过海量数据分析后,得出的能让“常态区”居民在被强制唤醒时,不至于产生过高“负面情绪阈值”的“黄金缓冲时间”,还是仅仅为了彰显BRC系统那无所不在的、对时间近乎偏执的掌控力?这种无聊的念头,如同他每天清晨睁眼时,鼻腔里那股子混合着消毒水、空气净化剂和某种难以名状的金属腐蚀气味的“常态区标准空气”一样,挥之不去,却又毫无意义。
窗外的天,永远是那种令人绝望的铅灰色,像一块被工业废气和高浓度信息素反复浸泡过的、失去了所有弹性的旧海绵,死气沉沉地覆盖着鳞次栉比、高耸入云的模块化公寓楼群。你永远看不见真正的太阳,也见不着皎洁的月亮,只有一片均匀的、压抑的、仿佛能拧出工业废水来的灰。底下,统一制式的磁悬浮通勤交通工具,像一节节被精确切割得整整齐齐的灰色金属香肠,在预设的、闪烁着微弱蓝色光芒的磁力轨道上,发出一种单调的、类似大型鼓风机在密闭空间内低频运转的“嗡嗡”声,又像是无数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巨大飞蛾在徒劳地振翅。它们载着同样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得如同被抽走了灵魂的人们,如同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提线木偶,汇入城市这部巨大精密、却又冰冷无情的机器的血管。
沈星住的“蜂巢公寓”,C栋734室,一个刚好能放下一张可以折叠收纳进墙壁的单人床、一个集成式声控盥洗单元和一个只提供标准营养液配给的嵌入式终端的逼仄空间。这里的墙壁薄得像纸,他能清晰地听到隔壁老王那如同拉风箱般的鼾声,楼上那个刚成年的小年轻半夜在虚拟现实格斗游戏中声嘶力竭的咆哮,以及楼下那对夫妻因为孩子的BRC教育系统评级又下降了零点三个百分点而爆发的、压抑着却又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激烈争吵。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子复杂的味道:楼下24小时运转的公共пище处理中心飘上来的、营养膏7号和再生蛋白棒在微波加热后产生的、带着一丝令人反胃的塑料甜腻的古怪香味;楼道里每隔三小时便会自动喷洒的、号称能杀灭99.99%已知病毒和细菌、却让人的鼻粘膜感到微微刺痛的消毒水味儿;还有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老旧机器的金属齿轮在缺乏润滑的情况下长期运转、金属部件在潮湿空气中缓慢氧化生锈后产生的“锈味”。沈星觉得,这“锈味”,才是这“蜂巢公寓”乃至整个“常态区”最真实、最核心的底色,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深入骨髓的、缓慢腐朽的味道。
他慢吞吞地从那张硬得像铁板一样的床上爬起来,身上那件印着奇点集团最新推广的“拥抱数据,链接未来”宣传标语的免费配发睡衣,因为劣质的合成纤维材质,已经洗得发白起球,穿在身上有种轻微的刺痒感。窗外,是更高、更密集的、同样色调单一、造型呆板的建筑群,像一片用水泥、合金和强化玻璃浇筑的、了无生气的、令人窒息的灰色森林。巨大的、占据了整栋楼宇外墙的全息广告牌在楼宇之间无声地闪烁、变幻,循环播放着奇点集团最新的企业形象宣传片——几个穿着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光鲜亮丽“精英人士”,他们的笑容标准到可以用几何公式来计算,在窗明几净、充满了未来科技感的虚拟实验室里,优雅地操作着一些闪烁着炫目光芒、却看不出具体用途的仪器,用一种经过BRC系统优化过的、充满了磁性和煽动性的声音,说着一些关于“无限可能”、“数据赋能”、“意识永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洞而乏味的口号。沈星每次看到这些广告,都觉得像是隔壁那个因为BRC社交成瘾而变得有些神经质的王大妈,在用一种打了鸡血般的、声情并茂的语调,朗诵一本由BRC-Core自动生成的、他一个字都理解不了其真实含义的天书。热闹是他们的,而他沈星,什么也没有,除了这间弥漫着“锈味”的鸽子笼。
沈星在奇点集团下属的一个庞大到他连其完整组织架构图都懒得去BRC内网查询的机构里上班,他的工牌上用最小号的字体印着一行卑微的部门名称:“泛社会信息流数据净化中心-东亚第七大区分部-初级人工审核岗”。说白了,就是个在数据信息时代这条巨大流水线上拧螺丝的苦力,而且还是最不起眼、最容易被替换掉的那种。
他的工作,就是在BRC网络通过复杂算法自动抓取、分类并初步筛选后的、如同汪洋大海般无穷无尽的、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普通BRC用户上传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毫无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生活片段信息流中,进一步人工复核并标记出那些可能包含“异常”情绪波动、“潜在违规”内容或“低价值冗余信息”的数据。
比如,某个用户在BRC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长达三十分钟的、关于他家宠物猫打哈欠的超高清视频,系统会自动将其标记为“低价值冗余信息,建议压缩存储或定期清理”;如果某个用户在匿名情感交流区发表了一篇痛斥奇点集团最新配给的营养液口味像下水道污水的帖子,并获得了超过十个“点赞”,系统会自动将其标记为“低烈度负面集体情绪事件,建议启动舆情引导预案”;如果某个用户在虚拟现实竞技游戏中因为连续输掉一百场排位赛而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和毁灭一切的愤怒情绪,并在公共频道发表了包含大量违禁词汇的过激言论,系统则会将其标记为“中度个体情绪失控,已触发BRC情绪平衡干预程序,建议列入重点观察名单”。
沈星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地面对着这些由冰冷数据构成的、光怪陆离的“人间百态”,然后用同样冰冷和麻木的手指,在BRC系统给出的选项上点击“同意标记”、“修正标记”或“驳回标记”。至于这些被他标记过的数据最终会流向何方,那些所谓的“异常”情绪是否真的会被BRC系统“温柔”地“平衡”掉,那些所谓的“违规”内容是否会被彻底“净化”得无影无踪,他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兴趣去知道。反正,他的KPI考核标准,只跟他每天处理的数据量和标记的“准确率”挂钩。他就像一个古代宫廷里负责给皇帝筛选奏折的小太监,每天经手无数关乎天下苍生命运的文书,但他自己,却永远只是那个卑微的、随时可能因为一点小错就被拖出去砍掉脑袋的奴才。
他每天骑着一辆锈迹斑斑、链条松垮、刹车失灵的“二八大杠”改装电动自行车上下班。这辆车是他从“常态区”边缘一个被戏称为“科技坟场”的巨型废品回收站里,用他积攒了三个月的NC(神经货币)兑换券淘换来的。车架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据说是某个已经消失的小国家生产的,上面还残留着一些早已褪色模糊的、他看不懂的异国文字。他用从各种报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零件,叮叮当当、七拼八凑地给它装上了一个功率小得可怜的二手电动机和一块容量堪忧、不知道还能充放电几次的劣质固态电池。每次骑在那些平整光滑、专为磁悬浮车辆设计的城市快速路上,他这辆破车都会发出一种像是得了几十年老慢支一样的“咯吱咯吱”、“嘎啦嘎啦”的噪音,引来无数乘坐着高效、静音、自带BRC环境舒适度调节系统的磁悬浮通勤工具的“体面人”鄙夷和嘲笑的目光。在这个人人都追求极致效率和完美体验的时代,他这辆破车,以及骑着这辆破车的他,无疑都是这个光鲜亮丽的“常态区”里一个极其碍眼的、不合时宜的异类。
自行车那同样锈迹斑斑的车筐里,常年固定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那是他从父亲沈建国留下的不多的遗物中翻出来的。缸子用了不知道多少年,杯口边缘的搪瓷已经因为长年累月的磕碰而掉落了好几大块,露出了里面被氧化得发黑的铁皮,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嘴里残缺不全、摇摇欲坠的几颗牙。他用这个缸子喝水,用它当碗泡那些难以下咽的营养速食面,甚至在加班到深夜、公寓楼的热水供应系统又出故障的时候,用它接过消防龙头里的冷水简单擦拭身体。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用着奇点集团最新配发的、自带BRC芯片、可以实时监测水质、自动调节水温、甚至能根据你的情绪状态推送不同口味“健康饮品配方”的智能水杯。只有他,还固执地、近乎偏执地用着这个在别人看来早已应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老古董”。
在那个如同巨大灰色蜂巢般的“数据净化中心”,同事之间的交流,少得可怜,也浅得可怜,浅得就像盛夏午后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出的那一层薄薄的水汽,你以为能抓住点什么,伸出手去,却只有一片虚无的灼热。大家每天肩并肩、面对面地坐在冰冷的、符合人体工学标准却让人腰酸背痛的工位上,头顶着同样无处不在的BRC网络信号覆盖,呼吸着同样由中央空调系统送来的、带着标准消毒水味和那股子熟悉“锈味”的循环空气,但彼此之间,却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坚不可摧的、完全透明的玻璃墙。你能看见对方的脸,能听见对方敲击虚拟键盘的声音,甚至能通过BRC公共信息流感知到对方因为长时间工作而产生的轻微生理疲惫信号,但你永远无法真正触碰到对方的内心,也无从知晓那张被BRC系统精心“优化”过的标准化表情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实情绪。
偶尔的、不得不进行的对话,内容也大多乏善可陈,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样,像是被BRC系统预设好的标准对话模板:BRC操作系统又更新了哪个版本的内核补丁,据说修复了上个版本中某些“可能导致用户产生不必要思考”的“潜在BUG”;奇点集团这个季度又统一配发了什么新口味的“福利”营养液,广告上宣称能“有效提升工作愉悦度百分之三点五七”;或者就是对某些被BRC网络严格屏蔽的、关于遥远的“例外区域”或者那些如同都市传说般的“天痕异闻”的、混杂着恐惧与好奇的捕风捉影的猜测和以讹传讹的“内部消息”。没有人会主动谈论自己的真实感受,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对方的喜怒哀乐,所有的人际交往,都像是被一台无形的、精密的程序所操控着,在预设好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运行,不偏不倚,不多不少。
沈星的工位斜对面,坐着一个名叫李梅的中年女人,她的BRC个人公开签名档常年挂着一行闪烁着柔和光芒的艺术字体:“生活因数据而多彩,生命因链接而永恒。感恩奇点,感恩BRC。”但沈星不止一次在午休时间,通过他那个“瑕疵品”接口偶尔捕捉到的、未经过滤的BRC公共信息流的细微异常波动中,“听”到她在那些被标记为“高风险匿名情感宣泄区”的、据说只有通过特殊手段才能访问的地下网络论坛里,用最粗俗、最恶毒、最不堪入耳的语言,疯狂地咒骂她的顶头上司是个“脑满肠肥的蠢猪”,咒骂这个“把人当狗一样使唤的操蛋世界”,咒骂奇点集团和它那个该死的BRC系统。当然,这些充满了原始愤怒和绝望的“异常情绪波动”,很快就会被无处不在的BRC网络监控系统精确地侦测到,并立刻启动相应的“温柔”而高效的“情绪平衡干预程序”。也许是一段精心剪辑的、充满了阳光沙滩和小猫小狗的“治愈系”短视频,也许是一首能直接作用于神经中枢的“α波舒缓音乐”,也许是强制推送的、关于某个“通过努力奋斗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的“模范员工”的励志故事。第二天,李梅又会准时出现在工位上,脸上重新挂上那副“阳光感恩”、“多彩永恒”的标准化表情,仿佛昨晚那个在网络深处声嘶力竭、如同疯兽般咆哮的女人,只是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早已被清除干净的梦魇。
至于“蜂巢公寓”里的邻里之间,更是形同陌路,甚至连“陌生人”这个词都显得有些过于亲近了。他们更像是一群被关在同一个巨大蚁穴里,却又被透明隔板隔开的、永不相交的蚂蚁。沈星能清晰地听到隔壁那个据说曾经是某个小公司老板、后来破产了只能靠领取BRC社会保障金度日的老王,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如同老式蒸汽火车头般惊天动地的鼾声;他也能清晰地听到楼上那个刚成年的、据说沉迷于一款名为“星际角斗场”的超拟真虚拟现实格斗游戏的小年轻,每天半夜因为在游戏里被人一次次虐杀而爆发出的、充满了不甘和屈辱的、声嘶力竭的大呼小叫;他还能清晰地听到楼下那对年轻夫妻,因为他们那个刚上小学的孩子的BRC教育系统综合评级又比上个月下降了零点三个百分点,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升入“精英预备班”的几率,而爆发出的、虽然刻意压低了音量却依然充满了焦虑、指责和歇斯底里的激烈争吵。但他们彼此之间,从未在楼道里打过一个照面,从未说过一句哪怕是最简单的问候。每个人都像一只高度警惕的蜗牛,把自己那脆弱而敏感的灵魂,紧紧地缩在由BRC网络为他们精心构建的、看似安全舒适、实则冰冷坚硬的数字硬壳里。
沈星早已习惯了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甚至在某种难以言说的程度上,他有些病态地享受着这种不被打扰的、绝对的“安全感”。至少,在这里,没有人会来窥探他内心深处那些不合时宜的真实想法,没有人会来质疑他那辆锈迹斑斑的“二八大杠”和他那个边缘掉漆的搪瓷缸子,更没有人会因为他后颈那个“瑕疵品”接口而投来异样的目光。
在这个时代,BRC(Bio-Resonant Cipher /生物谐振密文芯片)网络,就是神,就是空气,就是水,就是你赖以生存的一切,也是你永远无法摆脱的囚笼。
从你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甚至在你还在母亲子宫里孕育的时候,一枚米粒大小的、由奇点集团垄断生产和植入的最新型号BRC生物谐振密文芯片,就会通过微创手术,被精准地植入你的后颈神经束。它将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复制的身份标识。你的衣食住行,你的工作学习,你的社交娱乐,你的医疗保障,你的金融交易(通过一种被称为“神经货币”或NC的、与个体BRC活动数据直接挂钩的数字加密货币进行),所有的一切,都与这个小小的芯片深度绑定,密不可分。
BRC网络无孔不入,如同亿万条看不见的神经触手,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渗透进每一个个体的意识深处。它不仅记录着你的一言一行,分析着你的消费习惯,预测着你的行为模式,更在以一种你几乎无法察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你的思想,调控着你的情感。当你感到悲伤或愤怒时,BRC系统会自动为你推送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积极正能量”的定制化信息流,或者在你的听觉神经中播放一段能直接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的“情绪平衡引导音频”,确保你始终保持在一个“健康”、“稳定”、“积极向上”、“对社会生产力有益”的情绪区间内。
但沈星后颈那个被他父亲沈建国在二十多年前亲手植入的、据说是奇点集团最早期的、仅用于内部技术验证的“老旧型号BRC接口”,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中的异类,一个被时代彻底抛弃的“活化石”。
它的功能极其原始和受限,很多现代BRC网络早已普及的新功能它都完全无法兼容。比如,它无法流畅接收和处理那些需要极高神经带宽的、7D全息沉浸式虚拟现实娱乐信息流,当别人都在虚拟世界里体验着上天入地、改写历史的刺激时,他最多只能在BRC公共频道看看那些画质粗糙、内容乏味的二维公益宣传片。它也无法稳定接入那些需要进行深度神经数据交换和多重情感信息同步的“高阶虚拟社交网络”,当别人都在虚拟社区里呼朋引伴、体验着“比真实更真实”的社交乐趣时,他只能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那些早已无人问津的、充斥着乱码和BUG的早期BBS论坛里游荡。
更糟糕的是,这个“老古董”接口还极不稳定,时不时就会出些莫名其妙的“小毛病”。有时会突然传来一阵阵轻微的、如同被无数只小蚂蚁同时啃噬般的电流刺痛感,让他头皮发麻,眼前发黑;有时又会在一片万籁俱寂的深夜,或者在他精神极度疲惫、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在他的听觉神经中捕捉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毫无逻辑的、意义不明的杂音——有时像是老旧的短波收音机在信号不良的地区艰难地搜寻着早已消失的电台时发出的那种“沙沙沙”的背景噪音,有时又像是有人在距离他极其遥远的地方,用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充满了古老韵律和神秘力量的语言,窃窃私语,那些声音空灵、飘渺,却又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穿透力,仿佛能直接穿透他的头骨,在他大脑最深处的回响。
因为这个功能残缺、性能不稳、时不时还会“闹鬼”的“瑕疵品”接口,沈星在周围那些植入了最新型号BRC芯片、享受着完美数字生活的“正常人”眼中,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怪胎”和“被时代抛弃的落伍者”。同事们在午餐时兴高采烈地讨论着BRC网络上最新的虚拟偶像和沉浸式游戏时,会有意无意地避开他的目光,仿佛生怕被他身上那股子“落伍”的气息所“污染”。社区组织的“BRC家庭互助联谊活动”,他也从来没有收到过邀请。他曾经鼓起勇气,通过BRC婚恋匹配系统尝试寻找一个可以共度余生的伴侣,但每一次,当对方通过BRC数据交换,得知他后颈那个接口的型号和“健康状况”后,往往会立刻露出一种混合着同情、鄙夷和庆幸的、礼貌而疏远的标准化微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沈星对此感到深深的自卑和孤独,他不止一次在深夜里,用冰冷的自来水反复冲洗着后颈那个微微凸起的、带着一道陈旧疤痕的接口,幻想着能把它从自己身上彻底剥离出去。他也曾无数次下定决心,要去奇点集团指定的BRC官方升级服务中心,把这个该死的、给他带来了无尽烦恼和屈辱的“老古董”,换成最新型号的、功能强大、运行稳定、能让他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融入这个完美有序的数字时代的主流产品。
但他内心深处,却又对这个给他带来无尽痛苦的“瑕疵品”,抱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的、近乎病态的……庆幸和依赖。
他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沈建国还在世时,曾不止一次抚摸着他后颈的这个接口,用一种他当时完全听不懂的、充满了忧虑和期盼的复杂眼神看着他,反复叮嘱:“星仔,记住,这个东西,它不完美,甚至……很危险。但它也是……一道门,一道能让你在所有人都变成‘一样’的时候,还能保留一点点‘不一样’的门。永远……永远不要让任何人,轻易地关上这道门。除非……除非你找到了另一扇,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门。”
父亲的话,像一颗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种子,在他日复一日的麻木和绝望中,顽强地保留着一丝微弱的生机。
他隐隐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瑕疵品”的存在,因为它的功能受限和偶尔“失灵”,因为那些时不时传来的电流刺痛和意义不明的杂音,才让他与这个被BRC网络无孔不入地渗透、所有人都像是被同一个精密模具批量复制出来的、完美到令人窒息的世界,保留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却又弥足珍贵的距离。
仿佛只有通过那些被“正常人”视为故障和缺陷的“异常”体验,他才能一次又一次地确认,自己还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由意志(哪怕只是自以为的自由意志)的、活生生的、会感到痛苦、困惑和不甘的个体,而不是BRC庞大数据网络中一个可以被随意监控、修改、格式化甚至删除的、冰冷而驯服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