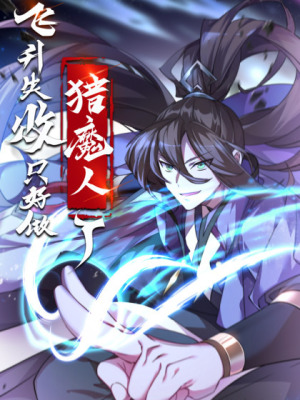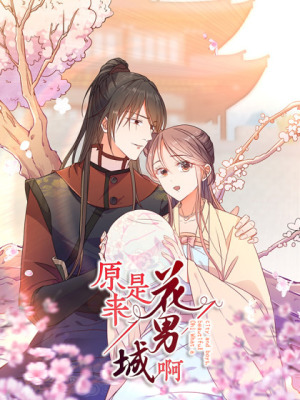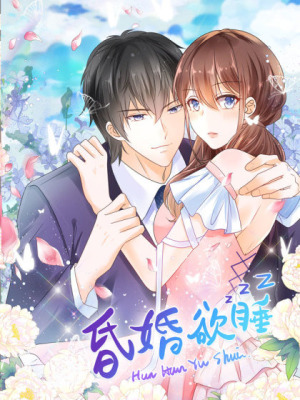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
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互联网人口,拥有跨越地域最辽阔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拥有一批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也拥有与世界同步的最新网络样态和技术实践。可以说,互联网已是中国在信息化时代傲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与此同时,我们对于网络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视也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容括了技术防控、政策因应、法理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的互联网安全措施正在逐次推进和不断深化。当然,在如此繁复、幽深、流动着巨量信息和蕴藏着惊人财富的网络世界里,法律不应缺席,也绝不缺席。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同样有着世界上类型最繁多的犯罪样式、构造最复杂的交易模式、数量最多的法律问题和最惊人的体量,这固然不值得赞许,但是客观上也给中国网络法的创生和发展提供了营养足够丰富的土壤。因此,对于网络法学研究而言,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最好的时代”。
现有的法律和司法体制模式,产生于农业社会,成熟和完备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不断转型、互联网迭代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面对信息时代和信息社会,如何实现法律和司法体制的代际发展与革命提升,是一个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重大问题。信息时代法律规则和理论的时代更新,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主张,而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网络法治实践贡献了不可估量的司法智慧,对于推动传统法律规则变革以适应信息时代,进而塑造信息时代自有的治理模式与法律规则,起到了先期探索的作用。16年来中国的网络法治实践,伴随着网络的迭代发展,实际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规则体系,在相当程度上走在了立法的前面。它的辐射范围,从最初的财产属性、电子证据、网络犯罪等热点问题,逐渐扩散至网络交易、网络不正当竞争、网络知识产权、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平台等领域,涵盖面越来越广,领域越来越深。以网络法中最棘手的网络犯罪为例,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相对稳定和缓慢,使得罪刑法定原则约束下的刑法能够较为顺利地应对实践中出现的绝大部分问题。但随着人类步入信息时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幅加快,各种新技术、新事物层出不穷,受罪刑法定原则“束缚”的刑法在面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时越来越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刑法在信息时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立法的途径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司法智慧的贡献度较之立法显得更为突出。基于秩序维护的需要而进行有节制的扩张解释,成为一种正在悄然进行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司法探索,也成为帮助传统刑法悄然迈入网络空间、网络世界的基本模式。通过一个个案件判决显示的司法智慧和确立的定罪量刑等领域的规则,悄然通过一桩桩案件不断进行展示,进而宣示,最终达成共识。因此,网络法的学习、研究乃至发展,需要格外重视案例的作用,重视大步前行的司法案件中的法理探索和判决结论。借助司法实践的个案处理,一方面,具有“短平快”的特点,能够及时回应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则能够以个案形式不断探索网络时代的法律规则,为今后的网络立法提供经验、铺平道路。以网络犯罪的四次迭代发展为例,网络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前网络时代—网络1.0时代—网络2.0时代—网络‘空间化’时代”四个阶段。前网络时代的犯罪主要是盗版软件问题,实际上并不涉及网络,也和计算机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属于“与计算机有关的犯罪”,计算机本身仅仅是盗版软件的读取工具和犯罪的“媒介”,因此当时立法上通过新增“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就能够解决;进入网络1.0时代,犯罪开始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主要表现为非法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将计算机本身作为“犯罪对象”加以侵害,于是通过两次立法,构建了我国计算机犯罪罪名体系,并通过后续的司法解释不断进行了完善与细化;踏入网络2.0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可能,点对点的犯罪也开始出现,传统犯罪在网络时代产生了异化,网络开始以“犯罪工具”的形象展现,于是立法和司法再次发力,立法上通过及时增设新罪名严密法网,司法上则变为与时俱进的司法解释出台,从这一时期的司法解释远远多于其他时期可见一斑;到了网络“空间化”时代,随着平台思维的兴起,网络成为滋生犯罪的空间与土壤,网络正式成为“犯罪空间”,此时刑法本身因尚未总结出规律和形成类型化的解决思路而稍有停滞,只能通过司法解释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网络犯罪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人类对网络深度利用而变化的,是网络自身不断升级发展的过程,更是网络逐渐“主体化”的过程。网络在网络犯罪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演变历程:媒介—对象—工具—空间。甚至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发展到“主体”这一阶段。与网络在犯罪中的地位发展历程相伴的是,网络犯罪侵犯的客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逐渐趋向整体化、抽象化:软件—系统—财产—秩序。如果按照网络未来的发展趋势,“人身”成为网络犯罪的客体或许将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因此,犯罪没有终点,网络犯罪也不会消亡,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顺应时代发展,更新观念,以应对不断升级变异的网络犯罪。
源自实践的司法智慧不断回应与填补网络时代的法律发展需求与漏洞,并以个案形式不断探索、点滴汇聚,最终反哺网络法律理论,促成网络立法的出台。同样以网络犯罪为例,作为两项重要的网络犯罪刑事立法思路,“帮助行为正犯化”和“预备行为实行化”就是源于实践的不断探索,进而反哺理论,最终上升为立法举措。二元化立法体制下“双重犯罪原则”导致的帮助犯难以处罚的尴尬、网络时代下帮助犯的危害性扩大与独立性提升、网络的虚拟性导致犯意无法证明等原因,使得实践中对网络犯罪的帮助犯如何定性与定量存在巨大争议。面对汹涌而来的现实案件,理论界通过实践归纳和分析,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突破传统共犯理论的做法,逐渐获得理论界的认可,最终反映到立法当中。这就是所谓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的内涵在于两方面,一是帮助犯“定性独立化”,二是帮助犯“评价正犯化”。“定性独立化”是指认定犯罪、追究责任时对于帮助犯可以脱离实行犯而单独、直接定罪;“评价正犯化”是指由于网络时代“一帮多”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技术性帮助行为的地位越发重要,传统理论中被视为从犯、共犯的帮助犯,在评价上应当被视为主犯、正犯予以量刑处罚。《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于网络犯罪的帮助犯予以独立入罪。“预备行为实行化”也是依照同样的轨迹发展。在社会不安全感加重的背景下,预防性犯罪化的巨大作用和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对于恐怖主义犯罪、重大网络犯罪等具有高危害特质的犯罪行为,刑法进行预先性防御的必要性激增。在立法的普遍处罚主义和司法的普遍不处罚主义的鸿沟面前,将部分危险性较高的“预备行为”法定化为“实行行为”,不失为一种可行做法。预备行为实行化是将原本属于其他犯罪的预备行为按照实行行为予以处罚。预备行为的实行化具有两个效果:一是对于预备行为处罚的独立化,这一点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是一致的;二是刑法打击时点的前移,如果高风险犯罪必须等到危害结果发生再去处罚,往往不能有效保护法益。《刑法》第287条之一规定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于利用网络设立违法犯罪的网站、通讯群组,以及发布违法犯罪信息的行为,予以定罪处理。
中国的网络法治实践对于搭建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从传统社会、传统空间通向网络社会、网络空间的无形之梯提供了无数“试点”。编织网络法治的法网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网络大国,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编织网络法治法网的实践样本与经验,更为国际社会建立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规则在网络法领域提供了可以一起积极努力和有所贡献的思路。随着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中国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的程度加深,中国网络法律和司法探索对于网络法治的经验值得国际分享,这是中国为世界网络法治发展提供的中国思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一部分。
于志刚
2018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