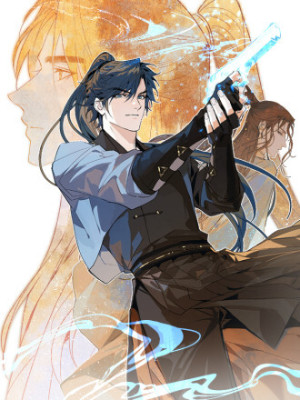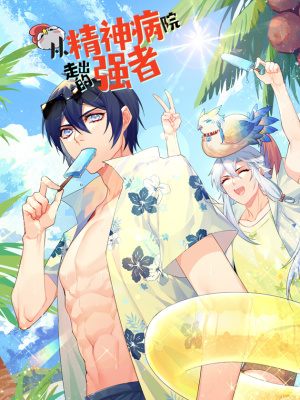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
《烽火长城》
第一章血染的番号
1937年的卢沟桥,月亮是红的。
赵铁军趴在宛平城的城墙上,手指抠着砖缝里的血痂。三八大盖的枪管被晒得发烫,烫得他虎口发麻。桥下的永定河泛着黑红的浪,漂着日军的钢盔和中国士兵的绑腿,河水拍打桥墩的声音,像无数人在水下呜咽。
“铁蛋,给老子递颗手榴弹!”班长王大锤的吼声震得他耳朵疼。东北汉子的胳膊上缠着浸血的绷带,那是昨天拼刺刀时被日军挑的,伤口还在渗血,染红了半截袖子。
赵铁军摸出颗木柄手榴弹,扯开引线递过去。王大锤接住,咬掉保险栓,像扔西瓜似的甩向冲锋的日军,爆炸声里混着惨叫声,几个黄皮膏药兵像被风吹倒的稻草人,栽进护城河里。
“他娘的,这群狗娘养的!”王大锤啐了口带血的唾沫,指着远处的坦克,“看见没?那铁疙瘩昨天压碎了老李的腿,咱得给老李报仇!”
赵铁军点点头,眼睛死死盯着日军的阵地。三天前他还是北平城里的学徒,跟着师傅在琉璃厂修古董,手里捏的是软布和糨糊。现在他握着枪,掌心的茧子是新磨的,枪托上还留着前位牺牲士兵的指痕,深得像刻进去的疤。
日军的冲锋号又响了,像招魂的唢呐。赵铁军学着老兵的样子,把枪管架在城垛上,瞄准最前面那个戴钢盔的日军。手指扣动扳机的瞬间,他想起了爹临走时的话。去年爹被抓去修炮楼,再也没回来,娘说爹是好样的,死也没给日本人当狗。
“砰!”子弹穿胸而过,日军像段木头栽倒在地。赵铁军的手还在抖,王大锤拍了拍他的背:“好小子,一枪爆头!比老子当年强!”
太阳落山时,日军的进攻停了。城墙上的尸体堆成了小山,有中国士兵的,也有日军的,血顺着砖缝往下流,在墙根汇成小小的溪流。赵铁军跟着王大锤清理战场,捡起能用的枪支弹药,手指碰过那些尚有余温的尸体,心里像被冰锥扎着疼。
“这是二连的番号。”王大锤从具尸体怀里掏出块染血的木牌,上面刻着“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110旅2连”,字迹被血泡得发胀,“得带着它,不能让二连断了根。”
赵铁军接过木牌,揣进怀里,紧贴着心口。木牌上的毛刺扎着皮肤,像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远处的日军营地亮起了火把,把夜空照得通红,像烧起来的晚霞。
“明天,咱得突围。”王大锤往嘴里灌了口烧酒,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流,“城里的弹药不多了,再守下去就是等死。”他把剩下的酒递给赵铁军,“喝点,壮胆。”
烧酒辣得赵铁军眼泪直流,却也暖了他发颤的手。他望着城墙下的永定河,想起小时候爹带他在河边放风筝,风筝飞得比城墙还高,线轴转得像风车。现在那只风筝恐怕早被炮弹炸成了碎片,就像这座他生活了十八年的城。
深夜,王大锤带着他们摸出宛平城,沿着永定河往西南走。赵铁军背着个受伤的小战士,那孩子才十五岁,比他还小,是昨天刚补进来的新兵,腿被炮弹片划伤了,疼得直哼哼,却咬着牙不吭声。
“疼就喊出来,没人笑话你。”赵铁军把水壶递给他。
小战士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个红绸子包,打开,是块冰糖:“俺娘给的,说含着就不疼了。”他掰了半块递给赵铁军,“你也含着。”
冰糖的甜味在嘴里化开,赵铁军却尝到了眼泪的咸味。他想起自己的娘,现在恐怕还在城里盼着他回去,手里捏着他没缝完的布鞋。
天快亮时,他们被日军发现了。照明弹像月亮似的挂在天上,把河滩照得如同白昼。王大锤喊了声“分散突围”,就抱着炸药包冲向追来的日军,爆炸声里,赵铁军看见他最后望了眼北平的方向,像在跟谁告别。
赵铁军背着小战士拼命跑,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身后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像过年时的鞭炮,却炸得人心里发慌。他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听见身后没了枪声,才瘫倒在芦苇丛里,大口喘着气。
小战士已经昏迷了,嘴唇干裂得像树皮。赵铁军解开水壶,往他嘴里滴了几滴 water,手指碰过孩子冰冷的脸颊,突然摸到他脖子上挂着的东西——是个小小的铜佛,被香火熏得发黑,佛肚子上刻着个“安”字。
“俺叫栓柱。”小战士迷迷糊糊地说,“俺爹是义和团的,说这佛能挡子弹……”
赵铁军把铜佛塞进他怀里,用布条裹紧。他摸了摸自己怀里的木牌,二连的番号还在,王大锤的烧酒壶还在,只是那个东北汉子,永远留在了永定河边的芦苇丛里。
远处传来了鸡叫声,天要亮了。赵铁军背起栓柱,朝着有炊烟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能活多久,但他知道,怀里的番号不能丢,就像爹说的,人可以死,骨头不能软。
风从芦苇丛里钻出来,带着河水的腥味,也带着硝烟的味道。赵铁军回头望了眼宛平城的方向,那里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像娘纳鞋底时用的白棉线。他握紧了手里的枪,枪托上的指痕硌着掌心,提醒他那些倒下的人,都在看着他往前走。
第二章敌后的星火
在玉米地里藏了七天后,赵铁军遇到了八路军。
那天他正背着栓柱找水喝,突然从玉米棵里钻出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枪口对着他们,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话文绉绉的:“同志,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
赵铁军看清他们臂章上的“八路”字样,突然松了口气,腿一软就倒在地上。这七天里,他们躲过日军的搜山队,吃过生玉米,喝过带虫子的泥水,栓柱的伤口发炎了,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不停地喊着“娘”。
“快,把伤员抬上担架!”戴眼镜的年轻人指挥着,自己蹲下来给赵铁军递水,“我叫李青山,是这支游击队的指导员。”
赵铁军接过水壶,一口气灌了半壶,水顺着下巴流进脖子,凉得他打了个哆嗦。他看着李青山的眼镜,镜片上有块裂痕,却擦得干干净净,像他说话的样子,透着股清亮。
游击队的根据地藏在个隐秘的山坳里,几十间土坯房,是村民们腾出来的。赵铁军跟着他们走进村子时,看见妇女们在碾米,孩子们在晒场上操练木棍,老人坐在门槛上卷烟,看见他们进来,都站起来打招呼,眼神里没有害怕,只有热乎劲儿。
“这是赵铁军,从前线撤下来的。”李青山把他领到间土房,“你先在这儿养伤,栓柱交给卫生员。”
土房里有张炕,铺着干净的稻草,墙角堆着些枪支弹药,擦得锃亮。赵铁军摸了摸那些枪,有的是老旧的汉阳造,有的是缴获的三八大盖,枪托上都刻着名字,有的是“张三”,有的是“李四”,还有的只刻着个“国”字。
“这些都是牺牲同志的枪。”李青山的声音有些沉,“我们留着,等新人来了,就把名字磨掉,刻上新的,这样队伍就永远有人。”
赵铁军的心猛地一动。他从怀里掏出那块二连的木牌,递给李青山:“这是29军二连的番号,还有人吗?”
李青山接过木牌,翻来覆去地看,眼睛突然红了:“二连……我知道他们,卢沟桥最能打的就是二连。现在……恐怕就剩你了。”他把木牌还给赵铁军,“你带着它,以后,你就是二连的根。”
接下来的日子,赵铁军跟着游击队活动。他学打游击,学埋地雷,学用土法造手榴弹。李青山教他认字,给他讲抗日的道理,说日本鬼子就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说中国就像这太行山,看着零散,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谁也拆不散。
栓柱的伤好了,跟着村里的孩子一起学认字,只是腿有点瘸,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却总抢着帮卫生员干活,说要学本事,以后能救更多人。他脖子上的铜佛被香火熏得更黑了,却说这是爹在天上看着他。
这天,李青山召集大家开会,说要去端日军的炮楼。那炮楼建在山口,卡住了游击队和外界的联系,里面住着一个班的日军,还有几十个伪军,经常下山抢粮,祸害老百姓。
“这是张寡妇的儿子,被炮楼里的伪军抓去当劳工,活活打死了。”李青山指着个哭红眼睛的妇女,“咱得给她报仇,也得把炮楼端了,打通这条道。”
赵铁军自告奋勇去炸炮楼的大门。他跟着王大锤学过怎么用炸药,知道怎么计算药量。夜里,他带着两个战士,摸到炮楼底下,把炸药包塞进大门缝里,拉响引线,转身就跑。
爆炸声震得山都在抖,炮楼的大门被炸塌了。游击队冲了进去,枪声、喊杀声、伪军的惨叫声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赵铁军举着枪,看见个伪军正想跑,他想起爹,想起王大锤,想起那些死在卢沟桥的弟兄,手指扣动了扳机。
战斗结束时,天刚蒙蒙亮。炮楼里的日军和伪军全被消灭了,游击队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还有几袋粮食,分给了村里的老百姓。张寡妇抱着儿子的遗物,跪在地上给战士们磕头,额头磕出了血,却笑着说:“俺儿可以瞑目了。”
赵铁军站在炮楼顶上,望着远处的太行山。山起伏连绵,像条沉睡的巨龙。李青山走到他身边,递给她一把新缴获的手枪:“这是给你的,勃朗宁,好用。”
赵铁军接过枪,掂量着,突然想起琉璃厂的师傅。师傅说,好的古董得有魂,好的枪也一样。他把二连的木牌系在枪上,红布条在风里飘着,像个小小的火把。
“以后,咱就叫‘长城队’。”李青山望着初升的太阳,声音清亮,“长城没倒,中国就没倒;队伍在,希望就在。”
赵铁军点点头,握紧了手里的枪。他知道,卢沟桥的硝烟还没散,永定河的水还在流,但他不再是那个只会修古董的学徒了。他是战士,是二连的根,是长城上的一块砖,就算碎了,也要扎在这片土地里,护着身后的乡亲,护着脚下的中国。
远处的山坡上,栓柱正带着孩子们操练,用木棍当枪,喊着整齐的口号,声音稚嫩却响亮,像破土而出的春芽,在烽火里倔强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