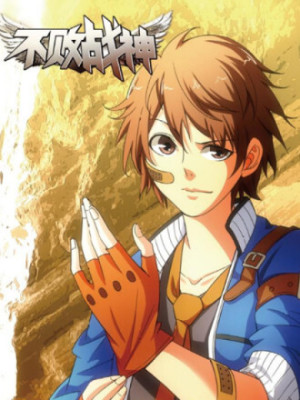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
青峦镇的雨,下得总带着股阴魂不散的黏腻。
不是那种倾盆而下的爽利,而是丝丝缕缕,无休无止,从铅灰色的低垂天幕里渗漏出来。它浸透了层层叠叠、铺满黛瓦的屋顶,让那些本已深沉的墨色显得愈发沉重,仿佛随时会不堪重负地坍塌下来。雨水顺着古老的瓦当滴落,在青石板铺就的窄巷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浑浊的水洼。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挥之不去的混合气息——新劈开的竹篾散发的微涩清香,长久阴湿角落悄然滋生的霉味,还有泥土被反复冲刷后泛起的、一种近乎腥甜的气息。
这湿冷,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
严明坐在一辆车身溅满泥点的老旧桑塔纳2000副驾上,车子正沿着盘山公路吃力地向上攀爬。车窗紧闭着,玻璃内侧凝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雾。他抬手,用指关节在雾气上划开一道狭长的缝隙,视线投向窗外。层峦叠嶂的墨绿山影在厚重的雨幕中若隐若现,山腰以上,便是翻涌不息、浓得化不开的灰白云海。山势陡峭,公路像一条湿漉漉的、垂死的巨蟒,紧紧缠绕着山体,每一次剧烈的转弯,都让车身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轮胎碾过湿滑的路面,发出令人不安的“嘶嘶”声。
“严队,前面就是青峦镇地界了。”开车的年轻警员小陈打破了沉默,声音在狭小的车厢里显得有些突兀,“这地方,邪性。您看这雨,从我们出市局就没停过。”
严明“嗯”了一声,目光没有离开窗外那片被雨雾吞噬的山色。他的侧脸线条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冷硬,眉宇间带着一种习惯性的、审视的凝重。保温杯里滚烫的枸杞水散发着微弱的热气,被他握在掌心,成了这湿冷世界里唯一一点实在的暖意。
车子拐过一个近乎直角的急弯,视野陡然开阔。一片依山而建的古老聚落,如同从水墨画里直接拓印出来,骤然撞入眼帘。深黑色的瓦顶连成一片起伏的海洋,在雨水的冲刷下闪着幽冷的光。一条浑浊的溪流,裹挟着山洪的蛮力,发出沉闷的咆哮,从镇子边缘奔腾而过。几座饱经风霜的石拱桥,如同沉默的老者,弓着背,顽强地跨在汹涌的溪水之上。
桑塔纳刚在镇口那棵虬枝盘曲、不知活了多少年的巨大老樟树下停稳,一个穿着湿透警用雨衣的身影就猛地从旁边昏暗的杂货店廊檐下冲了出来,几乎扑到了车前。雨衣的帽檐下,是一张年轻却写满惊惶的脸,嘴唇冻得有些发紫。
“严队!您可算来了!”声音又急又尖,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穿透了哗哗的雨声,“出大事了!就在……就在镇子后头的黑竹涧!捞上来了……捞上来了……”
严明推开车门,冰冷的雨点立刻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眉头一皱,沉声问:“捞上来什么?说清楚!”一股寒意,似乎比这山雨更刺骨,悄然爬上脊背。
“是……是林秀!”年轻片警喘着粗气,手指神经质地指向镇子深处,“林家那个在县里念高中的闺女!今天早上,采竹的老李头在黑竹涧的水湾里……发现的!人……人早就没了!”
林秀。这个名字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投入严明的心湖。他出发前匆匆翻阅过资料,死者身份确认得如此之快,本身就透着不寻常。
“现场呢?”严明的声音压得很低,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保护着呢!所长老刘亲自守着,不让任何人靠近!”片警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汗水混合物。
“带路!”严明不再多问,果断地拉上夹克的拉链,一头扎进漫天雨幕之中。小陈和片警紧随其后。三人的脚步声踏碎了石板路上的水洼,发出急促而空洞的回响。
通往黑竹涧的路愈发崎岖泥泞。茂密的竹林在风雨中狂乱地摇摆,细长的竹叶相互摩擦,发出持续不断的、令人心烦意乱的“沙沙”声,如同无数人在窃窃私语。脚下的路几乎被肆意流淌的泥水淹没,每一步都深陷其中,跋涉艰难。空气里那股混合着水腥、腐叶和竹子清冽气息的味道,浓烈得令人窒息。
黑竹涧并非什么壮阔的瀑布,只是一处较为陡峭的溪流跌落点。浑浊湍急的溪水在这里短暂地形成一个相对平缓的回水湾,水面上漂浮着大量被上游山洪裹挟下来的断枝、败叶和肮脏的泡沫。此刻,这个平日少有人迹的偏僻角落,却被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死寂笼罩着。几个穿着雨衣、脸色煞白的民警和几个明显是镇上壮汉的人,围在水湾边一片相对高些的泥滩上,形成一个松散的、压抑的圈。
圈子中心,一块临时找来的、边缘粗糙的暗绿色塑料布上,静静地躺着一个人形。
严明拨开人群,走了进去。雨水立刻顺着他的额发流下,模糊了视线,但他依旧清晰地看到了塑料布上的景象。
一个年轻的女孩。身上裹着溪涧里常见的、湿滑黏腻的深绿色水草和肮脏的淤泥,一件质地普通的浅蓝色连衣裙被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尚未完全发育的、青涩而僵硬的曲线。她的脸孔苍白浮肿,嘴唇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紫色,双目紧闭,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浑浊的水珠,像是凝固的泪。湿透的黑发凌乱地贴在脸颊和脖颈上,如同纠结的海藻。
最刺目的,是她纤细脖颈上那道深紫色的瘀痕,像一条丑陋的毒蛇,死死缠绕着生命曾经流淌过的地方。严明蹲下身,戴着手套的手指极其小心地触碰了一下那道痕迹。冰冷,僵硬,触感如同冰冷的橡胶。他的目光缓缓下移,落在女孩紧握成拳的右手上。
那只手攥得死紧,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仿佛在生命最后一刻,用尽了所有力气也要抓住什么。严明屏住呼吸,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极其轻柔地、一点一点地掰开那几根冰冷僵硬的手指。
一枚纸鹤,静静地躺在女孩湿透的掌心。
它已经被溪水泡得发胀变形,纸的边缘起了毛,颜色也褪得模糊不清,但那奇特的折痕却依然清晰可辨——翅膀的折叠方式异常繁复,带着一种近乎扭曲的锐角转折,鹤颈以一种正常人绝不会采用的角度拧着,尖锐的喙直直地刺向上方,整个形态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和邪气。这绝非寻常孩童或少女会折出的那种温顺优雅的纸鹤。
严明的心脏猛地一沉。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枚被死亡浸透的纸鹤放进一个透明的证物袋。冰冷的雨水顺着他的后颈流下,他却感觉不到丝毫凉意,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被未知之物攫住的寒意。
“谁第一个发现的?”严明站起身,声音在哗哗雨声中显得格外冷硬。
一个缩在人群后面、穿着破旧蓑衣、浑身抖得像风中秋叶的干瘦老头被推了出来。是老李头,采竹人。他牙齿打着颤,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惊恐:“是……是我……今早雨小了点,我想着来涧边看看水势,能不能捞点被水冲下来的好竹子……就……就看到水湾边漂着个东西……像……像个人……我拿竹竿子勾了一下……就……”他再也说不下去,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响,仿佛那冰冷的触感还缠绕在他的竹竿上。
“发现时,她手里就攥着这个?”严明举起那个装着纸鹤的证物袋。
老李头茫然地看了一眼,猛地摇头,又点头:“我……我没看清啊!吓都吓死了,哪敢细看!就……就看见她手里好像抓着点白乎乎的东西……像……像是纸?”
严明锐利的目光扫过周围每一个人的脸,捕捉着细微的表情变化。恐惧、茫然、事不关己的麻木……混杂在一起。他挥挥手:“小陈,仔细勘验现场,一寸都不要放过,尤其是死者被发现的位置和水流痕迹。老刘,”他看向镇派出所那位脸色同样难看的刘所长,“保护好尸体,等县局法医来。封锁消息,暂时不要惊动死者家属。”
“明白,严队!”老刘声音干涩地应道。
留下小陈和民警处理现场,严明决定先回镇上落脚点——镇东头一家挂着“悦来客栈”褪色招牌的老旧旅店。他需要换身干衣服,也需要一点时间整理脑中纷乱的线索。冰冷的湿衣贴在身上,寒意仿佛要钻透骨髓。
回去的路,有意无意地,他选择了穿过镇子中心。狭窄的石板路两旁,是些低矮的老旧店铺,卖些杂货、竹器、香烛纸钱之类。雨水沿着瓦檐流下,形成一道道细密的水帘。时间已近晌午,本该是有些烟火气的时候,可街道上却行人寥寥。偶有几个人影,也都是缩在自家屋檐下,沉默地看着这个穿着夹克、明显是外乡人的陌生面孔,目光如同冰冷的探针,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和一种深沉的、难以言喻的疏离。
这份沉默,在严明走到镇子中心那座规模宏大、飞檐翘角、即便在阴雨天也透着一股森严威压的“林氏宗祠”前时,达到了顶峰。
祠堂那两扇厚重的、漆皮斑驳的朱红色大门紧闭着。门前宽阔的石阶上,却异常地坐着七八个老人。有男有女,都穿着老旧的深色棉袄或罩衫。他们沉默地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如同一排凝固的、布满岁月裂痕的雕像。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张望,甚至连咳嗽声都没有。他们的目光,如同约好了一般,齐刷刷地聚焦在冒雨走来的严明身上。
那目光浑浊、空洞,却又像蕴藏着某种沉甸甸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欢迎,更不是悲痛。那是一种近乎漠然的、穿透了时间和世事的平静,平静之下,又似乎蛰伏着某种难以解读的、冰冷彻骨的洞悉。雨水顺着祠堂门楣上那些雕刻繁复的兽首滴落,砸在石阶上,发出单调而固执的“嗒、嗒”声,更衬得这片沉默如同实质的墙壁,沉重地横亘在严明面前。
严明脚步不由自主地顿了一下。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目光的重量,它们像无形的蛛网,缠绕上来,带着湿冷的、属于这个古老宗祠特有的气息——香烛、陈木、尘土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时间沉淀下的肃穆与阴郁。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目光平静地迎向那片沉默的审视,脚步重新变得稳定而有力,一步一步,踏着湿滑的石板路,从那些静默的老人面前走过。
雨点敲打着他的肩膀。祠堂石阶上,那一片无声的注视,如影随形。直到他拐过街角,走进“悦来客栈”那光线昏暗的门洞,那如芒在背的感觉才稍稍减弱。
客栈大堂里弥漫着一股潮湿木头混合着劣质烟草和陈年油烟的味道。胖胖的老板娘正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看到严明进来,也只是掀了掀眼皮,含糊地指了指楼上:“二楼最里头,门没锁。”语气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仿佛进来的不是一个浑身湿透、带着山涧寒气的警察,而只是一个寻常的、不值得多看一眼的过客。
严明没说什么,径直走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二楼走廊幽深昏暗,尽头那间房的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房间很小,陈设简陋,只有一张硬板床,一张掉漆的桌子和一把椅子。一扇狭小的木窗对着客栈的后院,院里堆着些杂物,同样湿漉漉的。空气里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他脱下湿透的夹克和毛衣,挂在椅背上,只穿着一件贴身的背心。冰冷的空气立刻贴上皮肤,激起一层细小的栗粒。他走到窗边,想透口气,目光却下意识地投向窗外阴沉的天空和远处被雨雾笼罩的山峦轮廓。青峦镇……这名字此刻听来,竟带着一种不祥的谶意。
就在这时,他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是县局法医老周,一个经验丰富、言语向来简洁直接的老搭档。
“老严,”老周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却异常清晰,“青峦镇那个女娃的初步尸检,有点意思。”
严明的心提了起来:“说。”
“窒息死亡确定无疑。颈部索沟明显,符合生前被勒扼的特征。舌骨有骨折。死亡时间初步推断在昨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没有发现明显性侵迹象。”老周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种专业性的冷酷,“但是,有意思的来了。我们在她指甲缝里,提取到了不属于她自己的皮肤组织和少量男性衣物纤维。很新,是搏斗反抗时留下的。还有,”他的声音更沉了,“我们在她胃内容物里,检测出了残留的酒精成分,以及……某种特定的、在本地年轻人里私下流行的所谓‘约会’饮料的成分。浓度不低。”
严明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约会’饮料?催情的那种?”
“嗯,地下作坊弄的三无产品,加了点西地那非和别的乱七八糟的兴奋剂。成分很糙。”老周语气带着厌恶,“结合她指甲缝里的东西,还有那种死亡时间……老严,这初步看着,像是一起熟人作案的情杀或者奸杀未遂后杀人灭口。激情犯罪的可能性很高。动机和嫌疑人范围,应该不难划。”
情杀?
严明脑海里瞬间闪过林秀那张苍白浮肿的脸,还有她颈上那道致命的勒痕。一个青春正好的女学生,在雨夜,约会,饮料……激情犯罪?这似乎是一条清晰得近乎顺理成章的脉络。法医的初步判断指向明确。
然而……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丢在床上的那个透明证物袋。那枚被溪水浸泡过的纸鹤躺在里面,怪异的折痕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扭曲、刺眼。那冰冷的溪水,那祠堂门口沉默得令人心悸的老人,还有老李头惊恐眼神中残留的、对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惧……这些碎片,和“情杀”这个冰冷的结论格格不入。
纸鹤。这诡异的纸鹤,在法医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它似乎成了一个突兀的、被排除在冰冷逻辑之外的幽灵符号。
“知道了。详细报告出来第一时间给我。”严明挂了电话。房间里只剩下窗外淅沥的雨声和他自己的呼吸声。
他走到床边,拿起那个证物袋,对着昏暗的光线,再次仔细端详那只纸鹤。那扭曲的翅膀,拧转的脖颈,尖锐的喙……越看,越觉得那折痕深处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邪气。这绝不是随手折就的东西。它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充满恶意的标记。
疲惫如同冰冷的潮水,夹杂着案情的沉重和这小镇无处不在的诡异氛围,汹涌地漫上来。严明重重地倒在硬板床上,连湿透的裤子也懒得换。木床发出痛苦的呻吟。他闭上眼,只想在这令人窒息的湿冷和疑云中,暂时地、哪怕只是片刻地,关闭所有的感官。
意识很快沉入一片混沌的黑暗。但黑暗并未带来安宁。
他感觉自己仿佛漂浮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冰冷的触感包裹了全身,带着溪涧深处那种特有的、带着淤泥腥气的寒意。他沉在幽暗的水底,四周是缓慢飘荡的水草。水波扭曲了光线,他看到无数惨白的影子在头顶晃动——是纸鹤。数不清的纸鹤,如同被惊起的幽灵鸟群,密密麻麻地悬浮在浑浊的水面之下。它们无声地扇动着被水浸透、沉重不堪的翅膀,动作僵硬而诡异,每一次扇动都搅起细小的、死亡的气泡。
翅膀扇动的声音……不,不是声音,是一种直接灌入脑海的、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嘶啦……嘶啦……像是粗糙的砂纸在反复刮擦着神经。
就在这令人头皮发麻的摩擦声里,一个极其细微、却又清晰得如同贴在耳膜上的声音,幽幽地渗了进来:
“下一个……”
那声音轻飘飘的,带着少女特有的清泠,却又浸透了水底的阴寒和一种非人的空洞。
“轮到你了……”
严明猛地睁开眼!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撞碎肋骨。冷汗瞬间浸透了背心,黏腻冰冷。他急促地喘息着,如同离水的鱼。房间里一片昏暗,只有窗外雨滴敲打瓦片的单调声响,更衬得梦里的死寂与那声耳语无比真实。
他撑着坐起身,手肘下意识地扫过冰凉的床头柜。
一个冰冷、微硬的触感,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背。
严明全身的血液在这一刹那几乎冻结!
他猛地转头,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最后一丝惨淡的天光,看清了床头柜靠近墙壁的角落里,静静地立着一样东西。
一枚崭新的纸鹤。
惨白的折纸,在昏暗中白得刺眼。翅膀以那种熟悉的、令人极度不适的锐角扭曲着,尖锐的喙,直直地指向他刚刚惊醒的脸庞。
折痕,与林秀手中那枚,一模一样。
“嘶……”
严明倒抽一口冷气,猛地从床上弹起,后背重重撞在冰冷的墙壁上。梦境里那冰冷溪水和漫天纸鹤的幻影尚未完全消散,眼前这枚突兀出现的惨白纸鹤,却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感,死死钉在视线里。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如同在无数次凶案现场所做的那样。没有立刻去碰触那枚纸鹤,锐利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迅速扫过整个房间。
狭小的空间一览无余。硬板床,掉漆的桌子,歪斜的椅子,挂着他湿外套的椅背。唯一的出口是那扇单薄的木门,门后的插销……他记得清清楚楚,进屋时,他亲手将那个锈迹斑斑的黄铜插销插进了锁槽!此刻,插销依旧牢牢地卡在锁槽里,纹丝未动。
窗户!他倏地转头看向那扇狭小的木窗。窗框老旧,窗栓是那种老式的铁扣。睡前他嫌闷,曾将窗户推开了一道一掌宽的缝隙透气。此刻,那缝隙依旧维持着原样,雨水正从缝隙边缘悄无声息地渗入,在窗台上积了一小滩水渍。窗外是客栈后院,堆着些破旧的竹筐和杂物,再远处,就是高耸的、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院墙。
从那条一掌宽的缝隙里塞进这样一枚纸鹤……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需要极度的精准和安静,并且要冒极大的风险——窗下就是人来人往(虽然今日人少)的后院通道。
严明的心沉了下去。无论是门还是窗,都指向一个事实:有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他刚刚陷入浅眠的片刻,如同一个技艺高超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这个被锁住的房间,放下了这枚死亡的“信物”,然后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他脑海中闪过客栈老板娘那张麻木的脸,以及楼下大堂那昏暗的光线,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念头升起:也许,这枚纸鹤,在他踏入这间房之前,就已经等在了这里?
他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入肺腑,强行压下翻腾的寒意和愤怒。戴上随身携带的取证手套,他极其小心地拿起那枚新的纸鹤。触手冰凉,纸张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种廉价白纸,带着新折痕特有的僵硬感。折法……他仔细对比着证物袋里林秀的那枚。是的,一模一样。那种扭曲翅膀的锐角转折,那种拧转脖颈的角度,那种尖锐得仿佛要刺破什么的喙……如同复刻。这绝非巧合。
是谁?目的是什么?恐吓?警告?还是某种……宣告?
严明将新发现的纸鹤也放入另一个证物袋。冰冷的塑料贴在掌心。他走到窗边,再次检查那道缝隙。窗台内侧的木头因为潮湿而颜色略深,但除了雨水的痕迹,没有明显的擦蹭或泥渍。他又蹲下身,仔细检查窗下的地面和床沿附近,同样干净得过分。
没有痕迹。就像那个潜入者,真的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幽灵。
他直起身,目光投向窗外。雨幕依旧浓重,将客栈的后院和远处的院墙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汽之中。院墙很高,顶上插着防止攀爬的碎玻璃,在雨水中闪着阴冷的光。墙外,是青峦镇层层叠叠、沉默矗立的黑色屋脊。
就在这时,一阵风吹过,卷着雨丝扑进窗缝。风中似乎隐约夹杂着一点细微的声响,像是……很多人同时发出的、极其压抑的叹息,又像是无数片竹叶在更远处、更密集的地方摩擦。
严明猛地关上窗户,插紧窗栓。木栓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他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手里紧紧攥着那两个装着纸鹤的证物袋。林秀冰冷的尸体、法医“情杀”的初步判断、祠堂前沉默如山的老人、诡异的噩梦、还有这枚不请自来的“死亡通知”……所有的线索和疑点,此刻都如同这青峦镇上空盘旋不散的雨云,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相互撕扯,却又隐隐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个看似平静、笼罩在雨雾中的古老山镇,其深处隐藏的东西,远比一桩简单的“情杀”要冰冷、黑暗得多。
“下一个……轮到你了……”
少女那空洞阴寒的耳语,仿佛又在死寂的房间里幽幽响起。
严明眼中最后一丝睡意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冰封般的锐利和一种近乎燃烧的凝重。他走到桌边,将那两枚代表死亡和不祥的纸鹤,并排放在桌面上。惨白的折纸在昏暗中散发着微弱而冰冷的光。
他拿出手机,拨通小陈的号码,声音低沉而稳定,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
“小陈,现场处理完立刻回来。另外,给我查清楚两件事:第一,林秀在镇上、学校里所有的人际关系,尤其是感情纠葛,重点排查昨晚九点到十一点有作案时间、与她有接触的年轻男性。第二,也是最重要的,给我查清楚,青峦镇关于‘纸鹤’,特别是这种诡异折法的纸鹤,有没有什么说法?传说?或者禁忌?”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再次扫过桌上那两枚沉默的纸鹤,补充道:
“尤其是……问问那些坐在祠堂门口的老人。问问他们,有没有听过‘山鬼’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