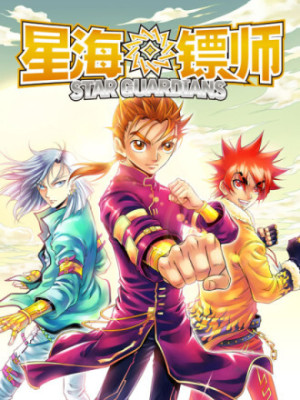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
(一)现在时- 2024年,纽约,冬夜
林晓月指尖划过冰凉的屏幕,族谱影像如水波般荡漾。窗外是曼哈顿不夜的灯火,窗内,她正试图用自己编写的AI算法,缝合一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家族记忆。
数据流在黑暗中奔腾,最终定格在一张经过算法增强的老照片上。照片上的男人穿着晚清长衫,面容清癯,眼神里有一种被时代磨损后的沉静。那是她的天祖,家族传奇的开端——林启源。照片旁注着时间:光绪二十一年,冬。公元1895年。
晓月的项目名为“回声”,旨在利用AI修复并理解家族散落在全球的史料。此刻,算法正试图还原一段家族口述史中提及的、林启源在得知《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反应。口述史只有一句模糊的话:“祖父闻讯,闭门三日,碎一茶盏。”
AI依据林启源后来的行为逻辑、同时代类似人物的日记、甚至当时的天气记录,模拟出了数个可能的情景。大多数模拟结果都指向悲愤、沉痛这些标准情绪。
然而,在筛选异常数据时,一段极不起眼的、来自林启源晚年日记的碎片,被AI标记为“高冲突值”。那是在事件发生二十年后,他只写了寥寥数字:
“是夜,星陨如雨。非为国运,乃为家计。一念之差,万劫不复,然未尝悔。”
“非为国运,乃为家计。”
“一念之差,万劫不复,然未尝悔。”
晓月反复咀嚼着这几句话,脊背窜上一股凉意。这和历史课本的叙事,和家族官方版本的“乡绅闻国耻而悲愤”,截然不同。那个夜晚,林启源真正思考的,竟然不是天下兴亡,而是…“家计”?那个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一念”,究竟是什么?
她放大那张1895年的照片。AI将像素修复得过于清晰,甚至能模拟出瞳孔的反光。晓月第一次发现,林启源那沉静的目光深处,似乎不是纯粹的悲愤,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混合了决绝、恐惧,甚至一丝…期待的神情。
一个被家族史精心掩盖了百余年的秘密,似乎正随着数据流的涌动,首次向她——这个拥有跨越太平洋血脉的第五代,透出一丝微光。
(二)过去时- 1895年,山海县,冬夜
星陨如雨。
林启源站在老宅书房的窗边,脑海里莫名浮现出这四个字。其实窗外并无流星,只有南方冬夜湿冷的、墨一般的黑暗,压得人喘不过气。
《马关条约》的消息,经由往来商船的传言和几日前抵达的《申报》,像瘟疫一样在山海县蔓延开来。割台、赔款,巨额的赔款最终会化作税银,压在每个像他这样的乡绅头上。国耻如山,压在心口。
但他此刻想的,确不只是国事。
桌上摊着的是家族田亩、商铺的账册,还有一封来自汕头的信,来自一位做南洋货生意的远房表亲。信里描述了南洋的机遇,提到了一条即将启航前往“狮城”的红头船。
“家计……”他无声地咀嚼着这两个字。林家数代积累,方有今日薄产。乱世将至,是固守祖业,在这显而易见的衰败中随波逐流?还是……另寻出路?
“一念之差,万劫不复。”他几乎能听到内心抉择时齿轮转动的巨响。
书房门被轻轻推开,妻子林陈氏端着一碗热茶走进来。她脚步很轻,像猫。她将茶碗放在桌上,没有看丈夫的脸,目光却落在了他下意识紧握的、微微颤抖的拳头上。
“孩子们都安置了。”她声音平和,听不出波澜,“嘉木在温书,嘉禾摆弄他那几个洋机器零件,嘉水……在房里绣花。”
林启源“嗯”了一声。他知道林陈氏说了谎。三女嘉水绝不会安分地在房里绣花,她此刻多半正躲在某处,偷读他那本夹带来的《时务报》。他没有点破。在这个家里,有些真相需要一层薄薄的纱布遮掩。
“这世道,要变了。”他像是在对妻子说,又像是自语。
林陈氏沉默片刻,才低声道:“世道再变,人总是要吃饭,要穿衣,要往前走。”
她的话像一枚石子,投入林启源翻涌的心湖。他回头,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妻子在油灯下显得有些模糊的侧脸。这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来的女人,他从未与她有过什么心灵相通的畅谈,但在此刻,他却从她这句最朴实无华的话里,汲取到一种奇异的、脚踏实地的力量。
“未尝悔……”一个念头鬼使神差地冒出来。
也就在这时,后院隐约传来一阵压抑的争吵声,夹杂着少女激动的语调和一个少年试图劝解的声音。是嘉水,还有次子嘉禾。
林启源的眉头骤然锁紧,刚才那一丝暖意瞬间冻结。他猛地转身,不再看窗外的黑暗,也不再看妻子,大步向门外走去。他的长衫下摆带起一阵风,刮得油灯火焰剧烈摇晃。
林陈氏没有动,也没有立刻跟上去。她只是伸出手,极其轻柔地,将丈夫刚才无意中碰到桌角、险些跌落的一只普通青瓷茶盏,往里面推了推。
她的指尖感受到瓷壁传来的微温。然后,她听到前厅传来林启源带着怒意的低吼:
“嘉水!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