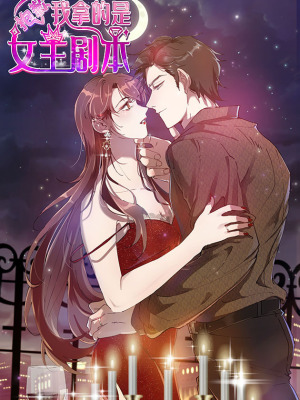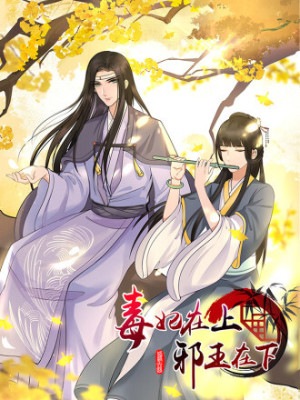好书等你评,快来成为鉴赏第一人
中和二年十月,长安城已冷得早。暮鼓初动,朱雀大街上的尘土被风卷着,像一层不肯落地的黄雾,把落日最后的血光也搅得浑浊不堪。李晏踩着鼓点往春明门外赶,怀里那卷刚抄完的《元和郡县图志》第三十二卷还留着墨香。他手指冻得发青,却仍用袖口把卷轴护得严实——赵郡李氏再没落,也容不得先祖手泽被北风吹残。
城门校尉认得他,却故意横矛:“李校书,酉时已过,莫非要犯夜?”李晏抬眼,看见那校尉甲胄内露出半片紫绢——田令孜新赐的神策军里衣。他垂首,从腰间摸出仅剩的两陌铜钱,在袖中掂了掂,递过去时顺势露出翰林院牙牌一角。校尉掂着铜钱笑,牙牌却让他笑意顿收:翰林院虽无实权,毕竟在天子眼皮下当差,闹大了,田军容也懒得为几个铜钱收场。于是矛尖一偏,让出仅容一人侧身的一线。
李晏道谢,声音被风吹碎。他出城,是为赶在日落前把书卷交还给城南龙首原的李府别业——那是李氏在长安最后的栖身处,三进小院,却藏着父亲李陟的棺柩。棺柩停殡已逾一年,无钱下葬。两陌铜钱原可雇四名力夫,如今进了校尉腰包,明日只能自己背土筑冢。想到这里,李晏胸口一阵钝痛,像有热铁慢慢烙在骨上。他咳嗽两声,掌心点点猩红,随手在袍角擦去——赵郡李氏的子弟,可以死,不可以狼狈。
夕阳沉到龙首原下,天边最后一道金线像被谁掐断,暮色轰然塌落。李府别业的门扉半倒,院内白幡早被风雨漂成灰黄,猎猎作响。李晏俯身,将图志放在棺侧,点燃一盏油灯,灯芯啪地炸出细小火星,照亮棺前那方无字木牌。他跪下去,额头抵地,声音低哑:“父亲,孩儿今日在弘文馆查得,元和十五年,先祖赞皇公曾奏设河北三镇互市,欲以盐铁换马,渐削藩镇之权。孩儿……想重提此策。”
话音未落,一阵风破门而入,灯焰骤暗,木牌倒下,正砸在他手背。生疼。李晏抬头,看见院墙缺口处,有人影一闪。他心头骤紧,却听那人轻唤:“可是李文潜?”声音压得极低,带着神策军特有的关西腔。李晏没应,手已摸向袖中短匕——那是他入翰林院第一月,用全部俸料钱换的百炼钢,刃薄如纸,专破内甲。人影却不再逼近,只抛来一物,落地轻响,是一枚折成方胜的紫麻纸。
李晏展开,纸上墨迹犹湿,只八个字:
“明日早朝,血诏焚楼。”
落款是一方朱印,印文却非朝廷任何衙司,而是一柄倒悬的剑。李晏认得——那是近日流传于坊间的“赤心社”暗记,传言为流亡宰相王铎与部分南衙朝官暗通声气所用。血诏?焚楼?他指尖发颤,却将纸凑近灯焰。火苗舔上紫麻纸,映得他眼底一片赤红。纸灰被风卷起,像一小群黑蝶,越过棺柩,越过无字木牌,消失在龙首原的夜色里。
更远处的长安城头,忽然亮起三朵号火,红黄青,次第高升。那是神策军夜防的讯号,也是田令孜给朱温、李克用等藩镇看的姿态:京师仍握在我手。李晏望着那三朵火,胸口钝痛再起,却比先前更冷。他想起白日里在弘文馆翻到的《秦中岁时记》,书中记天宝遗事,说玄宗曾在上元日放灯三万,火树银花,昼夜不息。如今同一座城,同一处原,火光却只剩戒备与杀意。
灯芯最后一跳,熄了。李晏在黑暗中端坐,听见自己心跳,像远方更鼓,一声,又一声,催他走向某个已无法回头的时辰。
纸灰散尽,龙首原上忽起朔风,吹得废园白幡猎猎如刀。李晏在棺前默坐片刻,忽听得墙外枯枝“咔嚓”一声,像有人踩断时间。他屏息,按匕循声而出,却只见荒草没膝,霜色映月,远处长安城堞的火炬排作一条蜿蜒金蛇,蛇头直抵西北——大明宫方向。
他回到屋内,取过一件半旧锦袍替棺柩遮尘。袍角绣着细碎的赤心花,是母亲生前所缝,一针一线尚带兰麝余香。指尖触到那花纹,他心底忽生荒唐念头:若真有血诏,若焚楼的是大明宫,母亲与先父会不会在九泉之下笑他迂腐?李氏一门自赞皇公李绛被乱兵所害,便再无人敢言“削藩”二字,偏他李晏,读了几卷残史,便以为能替将死的唐室续命。
念头甫起,他自嘲一笑,笑意牵动喉间腥甜,忙取案上冷茶压下。茶是昨日煎的,浮着一层黑沫,入口涩苦,却正合此时滋味。窗外忽传马嘶,短促而急,像有人在原地兜缰。李晏眉目一沉,将匕插入靴筒,推门而出。
月色如刃,照见篱外立一骑黑马,鞍上人身披玄甲,却未戴兜鍪,露出半张少年面孔,眉目锋利得近乎无情。少年抬手,抛来一只小小鱼袋,袋口勒得极紧,鼓胀如孕。李晏接过,指尖触到内里圆润冰凉——是一枚琉璃珠,珠心封着一点赤色,像凝住的血。少年低声道:“明日五更,丹凤门外,候诏。”说罢拨马欲走。
“且慢!”李晏踏前一步,“主事者何人?”
少年回头,眼底映着远处城火,像两粒烧红的炭:“欲知者,自去;不敢知者,自退。”话音未落,马蹄已溅起草间霜花,瞬息没入夜色。
李晏攥紧鱼袋,掌心被琉璃棱角硌得生疼。他忽然想起,今日午后在翰林院,同僚郑畋曾悄悄递给他半张残笺,上写“田令孜欲并盐铁、度支为一使,尽收财权以资神策”,旁注小字“王相公令诸司各上封事,冀延宕其议”。彼时他未在意,如今两相对照,一条暗线隐约浮现:南衙欲借外朝奏章,拖住田令孜聚敛之刃;田令孜则恐夜长梦多,或将于明日早朝强行颁诏,以“军兴费广”为由,焚毁三省旧案,重立盐铁新条——所谓“血诏焚楼”,竟是指焚尚书省后楼藏档,使朝臣再无旧例可援。
一念至此,他背脊骤寒。若让田令孜得逞,河北、江淮诸镇财赋尽归神策,朝廷与藩镇最后一丝制衡也将崩解。可“赤心社”竟将消息递给他这小小校书郎,分明是要他出头拦诏——拦得住,是替南衙夺一先机;拦不住,便是替死之羊。
李晏抬头望天,月色已斜,像一柄薄刃悬在长安头顶。他忽放声长笑,笑声惊起原上寒鸦,黑压压掠过废园,投下一片晃动的影。笑声止处,他低声自语:“李氏祖宗在上,孩儿纵死,亦当死于丹陛之下,不没于草莽。”
言罢,他返身入屋,启开一只斑驳竹箱,取出进士紫袍与平巾帻,以手熨平褶纹,挂于棺侧。接着点灯研墨,在素笺上疾书数行,字迹瘦硬如刀:
“臣晏言:盐铁旧案,系国计根本,若一夕尽焚,则诸道贡赋无凭,藩镇必借辞生衅。愿陛下缓其议,俟三司磨勘,然后施行。倘臣言不可用,请伏斧锧,以谢天下。”
写罢,他将素笺折作寸许小方,塞入鱼袋,与琉璃珠并置。灯焰摇曳,映得他面上血色如潮涨落。远处更鼓忽报四更,他整衣而起,推扉向东,长安城堞的火炬已半灭,唯大明宫方向仍有一片暗红,像未熄的炭,又像未凝的血。
李晏踏出废园,再不回顾。身后棺柩沉默,无字木牌倒在尘埃,像替他预先写好的墓碑。